白鸟逸话(5)
真可惜那天自己再次愣住了。一只白色的乌鸦,一双翅膀,一个喙和两条腿的纯白色的鸟,停在我的肩膀,藏在我的背后,一切我见不到的近处。反复发作的一切,是臆想,起因是我的病;在愈发炎热的夏季里愈发频繁地出现幻觉,不知何时起自己很难去分辨什么是幻境什么是现实,它们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一个死人浮出来,她的名字叫夏。留着恰当的头发,身穿碎花裙子,很白还很瘦;声音清脆,五官顶好看,言行举止虽然总让人不懂她想做些什么,不过某类单薄的极硬又极脆宛若冰片一样的,美丽且短暂的东西无疑在她身上发挥作用。
“阿良!”
夏是那种什么都好的女孩子。最妙的是她死得也很早,死人往往比活人漂亮。我们以前算熟悉,因为彼此的境遇相同。自我的妹妹展露出她不俗的天赋,母亲看不学无术的我愈觉得气愤,在我的父亲死后,我的母亲一直希望她的孩子也就是我成熟稳重些,最终我也一如既往。
夏的经历则更惨痛,她的母亲很久之前离家出走,她的父亲在她成人的一年前死于下班回家的台阶,她本人后来也死去。我们相识在一个秋天,那年夏自告奋勇地成为我的模特,还说一定要离开小城去旅行一次;我姑且留下了许多有关于夏的照片,记忆中她总是笑着的,像她死前也是笑着的。
“阿良!”
所以我选择了在地上对付一晚,由于种种原因:主因是酒醉的恍惚伙同剧烈的全身痉挛,以及站在身前不停呼唤的亡魂,如此触手可及站在暑气熏蒸的夜晚俯视我的脸,自己大概已经一败涂地。当时我冒出了自己将要死在这夏天的奇怪想法,如乌云密布时觉察天空要下一场无休无止的暴雨,像直觉或经历许多次暴雨后的经验。
“阿良!”
我总归是能忆起她的。一些蓝天上面数得过来的白云,一些在寂静中过头响的呼吸声,我目视一条仿佛亘古不变的河,手掌中紧握着摄影机,炎热消耗殆尽后的城中空无一人,世界的尽头处一位少女已站在围栏前方;轻盈如流风飘逸若回雪的她抬头,竭力想要捕捉一只白色的幻影。现在我知道她最终没能找到,留下的就只是一根或许洁白无瑕的羽毛,浮在半空中与整个世界融为一色,她却仍对天空扬起嘴角。
“阿良!”
而那事跟我没什么关系,有一双翅膀,一个喙和两条腿的,外形如同乌鸦又不是黑色,纯白色的鸟。我已眼神呆滞地背身离去,任凭梦中出现的白色乌鸦反复且无意义地腾飞在灰蒙蒙的城市上空,一遍遍穿过火力发电厂从烟囱中排放出的云;虽说我总是觉得很无聊,如同陷入深海的无能为力,无法转动我的头或向上浮起,更别提在黑暗里牢牢记忆海底风光。
一个死人浮出来,她的名字叫夏。留着恰当的头发,身穿碎花裙子,很白还很瘦;声音清脆,五官顶好看,言行举止虽然总让人不懂她想做些什么,不过某类单薄的极硬又极脆宛若冰片一样的,美丽且短暂的东西无疑在她身上发挥作用。
“阿良!”
夏是那种什么都好的女孩子。最妙的是她死得也很早,死人往往比活人漂亮。我们以前算熟悉,因为彼此的境遇相同。自我的妹妹展露出她不俗的天赋,母亲看不学无术的我愈觉得气愤,在我的父亲死后,我的母亲一直希望她的孩子也就是我成熟稳重些,最终我也一如既往。
夏的经历则更惨痛,她的母亲很久之前离家出走,她的父亲在她成人的一年前死于下班回家的台阶,她本人后来也死去。我们相识在一个秋天,那年夏自告奋勇地成为我的模特,还说一定要离开小城去旅行一次;我姑且留下了许多有关于夏的照片,记忆中她总是笑着的,像她死前也是笑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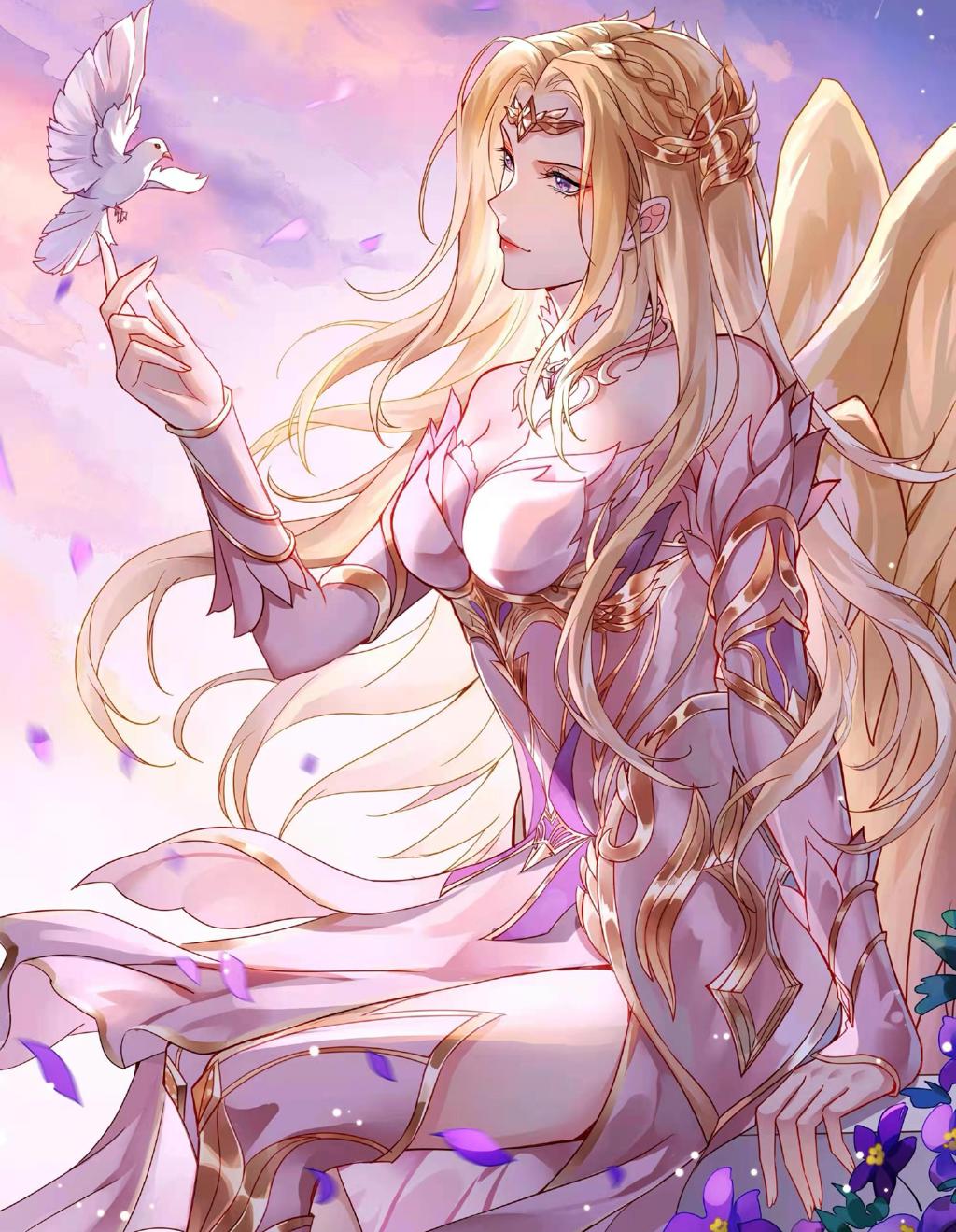
“阿良!”
所以我选择了在地上对付一晚,由于种种原因:主因是酒醉的恍惚伙同剧烈的全身痉挛,以及站在身前不停呼唤的亡魂,如此触手可及站在暑气熏蒸的夜晚俯视我的脸,自己大概已经一败涂地。当时我冒出了自己将要死在这夏天的奇怪想法,如乌云密布时觉察天空要下一场无休无止的暴雨,像直觉或经历许多次暴雨后的经验。
“阿良!”
我总归是能忆起她的。一些蓝天上面数得过来的白云,一些在寂静中过头响的呼吸声,我目视一条仿佛亘古不变的河,手掌中紧握着摄影机,炎热消耗殆尽后的城中空无一人,世界的尽头处一位少女已站在围栏前方;轻盈如流风飘逸若回雪的她抬头,竭力想要捕捉一只白色的幻影。现在我知道她最终没能找到,留下的就只是一根或许洁白无瑕的羽毛,浮在半空中与整个世界融为一色,她却仍对天空扬起嘴角。
“阿良!”
而那事跟我没什么关系,有一双翅膀,一个喙和两条腿的,外形如同乌鸦又不是黑色,纯白色的鸟。我已眼神呆滞地背身离去,任凭梦中出现的白色乌鸦反复且无意义地腾飞在灰蒙蒙的城市上空,一遍遍穿过火力发电厂从烟囱中排放出的云;虽说我总是觉得很无聊,如同陷入深海的无能为力,无法转动我的头或向上浮起,更别提在黑暗里牢牢记忆海底风光。

 光遇白鸟C到龙骨流白色液体
光遇白鸟C到龙骨流白色液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