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野抄》芥川龙之介(2)
两人不眨眼地瞅着师傅的病情。其角的身后是丈草,像是个出家人,手腕上挂着一串念珠,一动不动地端坐着。坐在丈草旁边的是乙州。不停地抽鼻涕,必是忍不住涌上来的悲哀吧。和尚打扮的矮个子惟然僧,正不转眼地盯着乙州。僧袍的袖子补了又补,表情冷漠地撅着下巴,同皮肤浅黑,有点刚愎自用的支考,并排坐在木节的对面。其余几个弟子,有的在左,有的在右,静悄悄地守着病床,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声。一个个为这死别,有无限的留恋难舍。可是,其中只有一个人,趴在屋角落里,紧贴在席子上,放声痛哭,那该是正秀吧?尽管如此,后客厅里,笼罩着冰冷的沉默,鸦雀无声,就连缭绕在枕边的线香,都一丝不乱。
方才,芭蕉一阵痰喘,用嘶哑的声音留下的遗言,让人无从捉摸。然后,就那么半睁着眼睛,像是昏睡了过去。脸上有几粒麻子,收得只剩下颧骨,四周布满皱纹的嘴唇,早就没有一丝血色。尤其叫人揪心的,是他那双眼睛,已经茫然无光,呆呆地望着远处,仿佛望着屋顶对面一望无际、意态清寒的天空似的。“病卧羁旅中,梦萦枯野上。”——这是他三四天前写下的辞世的俳句,此时,或许他就像自己所吟诵的那样,散乱的视线里,是荒郊枯野上的苍茫暮色,没有一星儿月光,如梦一般飘忽。
“水!”
半响,木节回过头来,冲着一动不动坐在身后的治郎兵卫吩咐道。这位老仆,早就把一盅水和一只羽毛做的牙签儿预备好了。他小心翼翼地把两样东西摆在主人的枕边,然后,又一心一意地急口念起佛号来。治郎兵卫是山里长大的,他以为芭蕉也好,恁谁也好,要想往生净土,一律得靠佛陀的慈悲。这种坚执的信念,在他朴实的心里,恐怕已经根深蒂固。
而另一方面,木节要水的一瞬间,忽然寻思道:身为大夫,自己果真想尽一切办法了么?这疑问一向就有,此时又冒出头来。他随即在自己心里勉励自己,而后转过脸,默默地朝身边的其角示意。也恰好在这当口,围着芭蕉病床的众弟子,心里猛然一紧,越发感到不安。可是,在紧张的前后,又有一种松口气的感觉——换句话说,要来的终于来了,如释重负一般,谁心里都闪过这个念头,这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这种如释重负的心情十分微妙,以致于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过这念头。在场的人里,数其角最讲实际,同木节面面相觑的刹那间,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出彼此心思一样。这时,连其角也没法儿不悚然一惊。他慌忙将视线移开,若无其事地拿起羽毛牙签。
方才,芭蕉一阵痰喘,用嘶哑的声音留下的遗言,让人无从捉摸。然后,就那么半睁着眼睛,像是昏睡了过去。脸上有几粒麻子,收得只剩下颧骨,四周布满皱纹的嘴唇,早就没有一丝血色。尤其叫人揪心的,是他那双眼睛,已经茫然无光,呆呆地望着远处,仿佛望着屋顶对面一望无际、意态清寒的天空似的。“病卧羁旅中,梦萦枯野上。”——这是他三四天前写下的辞世的俳句,此时,或许他就像自己所吟诵的那样,散乱的视线里,是荒郊枯野上的苍茫暮色,没有一星儿月光,如梦一般飘忽。

“水!”
半响,木节回过头来,冲着一动不动坐在身后的治郎兵卫吩咐道。这位老仆,早就把一盅水和一只羽毛做的牙签儿预备好了。他小心翼翼地把两样东西摆在主人的枕边,然后,又一心一意地急口念起佛号来。治郎兵卫是山里长大的,他以为芭蕉也好,恁谁也好,要想往生净土,一律得靠佛陀的慈悲。这种坚执的信念,在他朴实的心里,恐怕已经根深蒂固。
而另一方面,木节要水的一瞬间,忽然寻思道:身为大夫,自己果真想尽一切办法了么?这疑问一向就有,此时又冒出头来。他随即在自己心里勉励自己,而后转过脸,默默地朝身边的其角示意。也恰好在这当口,围着芭蕉病床的众弟子,心里猛然一紧,越发感到不安。可是,在紧张的前后,又有一种松口气的感觉——换句话说,要来的终于来了,如释重负一般,谁心里都闪过这个念头,这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这种如释重负的心情十分微妙,以致于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过这念头。在场的人里,数其角最讲实际,同木节面面相觑的刹那间,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出彼此心思一样。这时,连其角也没法儿不悚然一惊。他慌忙将视线移开,若无其事地拿起羽毛牙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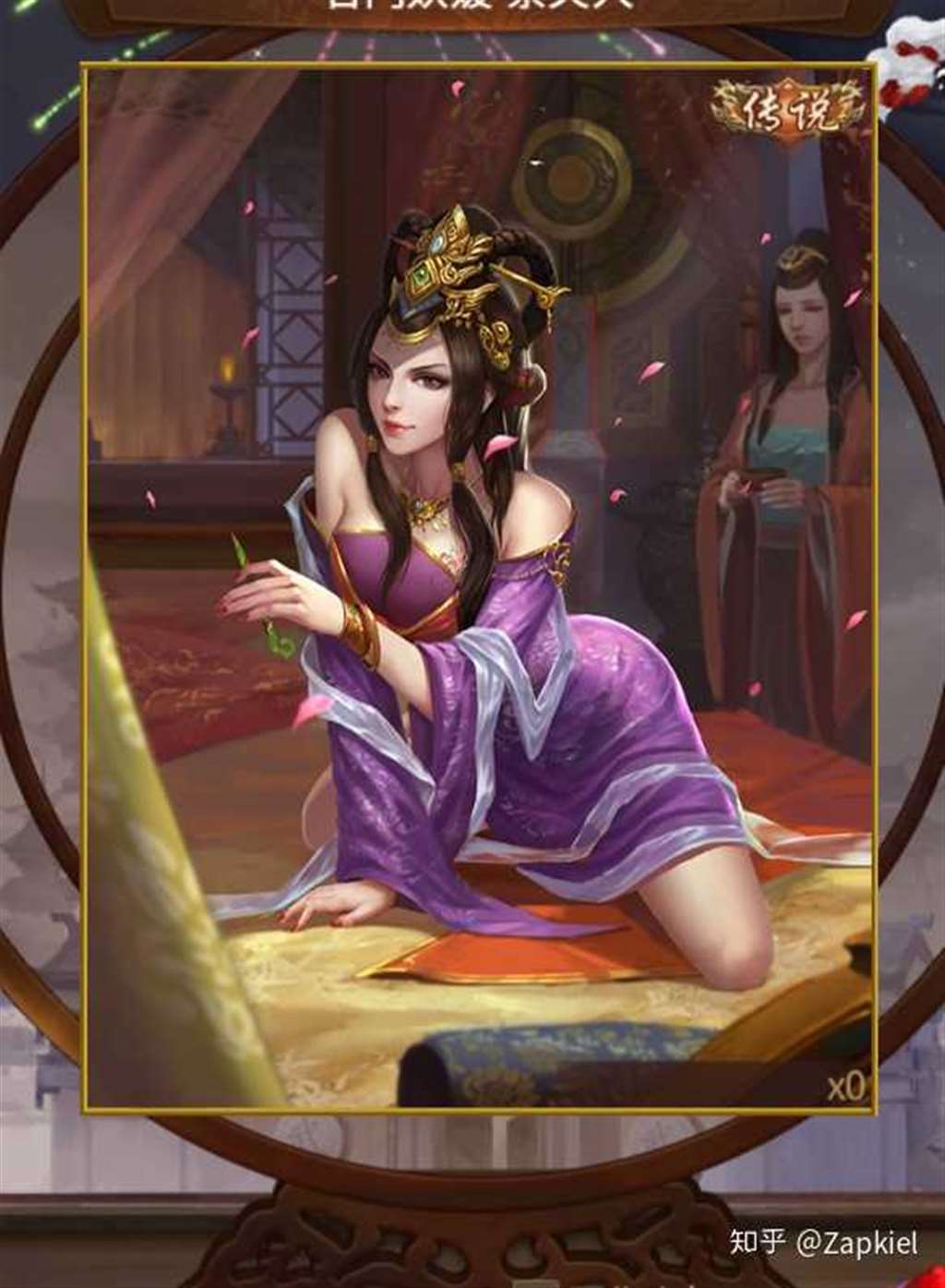
 沈泽川和萧驰野第一次
沈泽川和萧驰野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