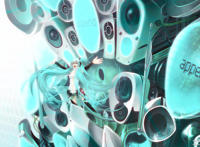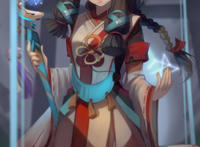玄怪录 卷三 吴全素(6)
两位官吏说:“钱的数量多,我们根本拿不动,但您是活人有力气,能够全部拿起来。请你背起这些钱,送去寄存起来。”全素起初认为这难以办到,试着用两只手往上提。用肩扛起它,巍峨耸立,极高极高,其实很轻。于是两位官吏引着他,把钱寄存在介公庙,庙里的神主穿着紫袍,腰间围着金带,命令小吏把钱收下。
寄完钱,两位官吏说:“您的还生是一定的了,是想马上回去,还是看点什么再回去?现在我们去捉拿一个人送他去投胎,能稍微看一下吗?”全素说:“这是我所希望的。”于是领着他进了西市绢行南边尽头的一户人家,那人家灯辉煌,家人在呜呜地哭泣,有几个和尚对着门在念经,满屋香烟缭绕,两个官吏不敢近前,于是从堂屋的后檐登上屋,估计对着睡床,又抽去屋瓦,拆开椽子,开了个大洞。从洞中看下去,一个老人气息奄奄,相对哭泣的人围着他的床。
一个官吏从怀里拿出绳索,有指头那么粗二丈多长,他叫全素坐好,拿着绳索的一头,把另一头从洞中放下去,告诫全素说:“我马上去捉拿那个人,一捉来,你应该拉绳索。”那官吏就下到房里,用右手揪住老人,用左手拉动绳索。全素急忙把老人拉了上来,拖在堂前,用绳索像捆囚犯似地把他绑起来。两个官吏轮换着把他背了出去,相互商量说:“那儿有最大的屠宰案桌?”其中的一个说:政坊十字街南边王家的屠宰案桌最大。”便一起到那里去。
走到那里,两人官吏把老人丢在屠宰案桌上,他俩脱下衣衫缠在身上,轮换着上去推转扑打,老人叫苦,那声音凄惨感人。全素说:“他如果有罪,应该依受刑罚;你们这样干,也是不合法的;如果没有罪,为什么折磨他?”
两个官吏说:“到这时候你才提出问题,我们感到惊讶。凡是有善功法德,该升天堂的人,有仙乐彩云、霓旌鹤驾来迎接他去,这种人我们怎么能见到?”如果有重罪和肮脏丑恶行径,该打入地狱的人,由牛头奇鬼带着铁叉枷铐来捉拿他,这种人我们又怎么能见到?这个老人没有升入天堂的福份,又没有下地狱的罪行,虽然能洁身自好,但没有离开尘俗,只是保持清白,没有污点。这个身子既然舍去了,就应该投胎去变成另一个男人。当地方官计算好的时候,他母亲已怀孕了,这个生命已经结束,那个生命应该诞生。现在如果不把他搓揉扑打,让那妇人怎么能生他呢?”于是,又用力揉搓扑打,确实感到老人的躯钵渐渐缩小。不一会躯体像只拳头那么大,肢体,眼耳口鼻,没有不像老样子的。
于是慢慢地提着他。他们走过子城大胜业坊,沿看。南方向直下再东回,在第二条小巷的北壁,走进第一户人家。那家也是灯火辉煌,人们在小声说话。有两个和尚,对着窗子念《八阳经》。这两个官吏不敢走近和尚,直接走上台阶,看见堂屋的门斜掩着,一个官吏提着老人,向堂屋走去,似乎刚落到床上,婴儿已经啼哭了。
寄完钱,两位官吏说:“您的还生是一定的了,是想马上回去,还是看点什么再回去?现在我们去捉拿一个人送他去投胎,能稍微看一下吗?”全素说:“这是我所希望的。”于是领着他进了西市绢行南边尽头的一户人家,那人家灯辉煌,家人在呜呜地哭泣,有几个和尚对着门在念经,满屋香烟缭绕,两个官吏不敢近前,于是从堂屋的后檐登上屋,估计对着睡床,又抽去屋瓦,拆开椽子,开了个大洞。从洞中看下去,一个老人气息奄奄,相对哭泣的人围着他的床。
一个官吏从怀里拿出绳索,有指头那么粗二丈多长,他叫全素坐好,拿着绳索的一头,把另一头从洞中放下去,告诫全素说:“我马上去捉拿那个人,一捉来,你应该拉绳索。”那官吏就下到房里,用右手揪住老人,用左手拉动绳索。全素急忙把老人拉了上来,拖在堂前,用绳索像捆囚犯似地把他绑起来。两个官吏轮换着把他背了出去,相互商量说:“那儿有最大的屠宰案桌?”其中的一个说:政坊十字街南边王家的屠宰案桌最大。”便一起到那里去。
走到那里,两人官吏把老人丢在屠宰案桌上,他俩脱下衣衫缠在身上,轮换着上去推转扑打,老人叫苦,那声音凄惨感人。全素说:“他如果有罪,应该依受刑罚;你们这样干,也是不合法的;如果没有罪,为什么折磨他?”
两个官吏说:“到这时候你才提出问题,我们感到惊讶。凡是有善功法德,该升天堂的人,有仙乐彩云、霓旌鹤驾来迎接他去,这种人我们怎么能见到?”如果有重罪和肮脏丑恶行径,该打入地狱的人,由牛头奇鬼带着铁叉枷铐来捉拿他,这种人我们又怎么能见到?这个老人没有升入天堂的福份,又没有下地狱的罪行,虽然能洁身自好,但没有离开尘俗,只是保持清白,没有污点。这个身子既然舍去了,就应该投胎去变成另一个男人。当地方官计算好的时候,他母亲已怀孕了,这个生命已经结束,那个生命应该诞生。现在如果不把他搓揉扑打,让那妇人怎么能生他呢?”于是,又用力揉搓扑打,确实感到老人的躯钵渐渐缩小。不一会躯体像只拳头那么大,肢体,眼耳口鼻,没有不像老样子的。
于是慢慢地提着他。他们走过子城大胜业坊,沿看。南方向直下再东回,在第二条小巷的北壁,走进第一户人家。那家也是灯火辉煌,人们在小声说话。有两个和尚,对着窗子念《八阳经》。这两个官吏不敢走近和尚,直接走上台阶,看见堂屋的门斜掩着,一个官吏提着老人,向堂屋走去,似乎刚落到床上,婴儿已经啼哭了。
 吾师第三卷挨打
吾师第三卷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