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组】梨园(《夕飨》的续篇)(4)
舞台前的空地早已为一群小孩子所占领了。他们手上各个拿着糖果红包之属,预计等大花旦一亮相,就朝她手里塞,然后听花旦姐姐——准确来说是剧中的赵五娘——对自己说一些学业有成的吉祥话。这些样子都是从他们的家长那辈教的,习俗说,戏班的演员们凡对小孩施上祝福,美言就能成真。虽然稍大一些的年轻人已经对这套东西不热心了。
随着这种说不上是迷信还是醇厚的习俗一道冷却的还有观戏的氛围。自从她一天天长大成人,同辈同学已逐渐不喜欢去看戏。有些人听上了磁带,有些人摇上了天线,厂里也买了吉他,建了兴趣室,一丛小青工爱好在那练谱玩。还有从前中专的男同学同她玩笑,说她从厂里考教师靠夜校,他从厂里考教师就靠吉他——奔着音乐老师去了。
在小时完全没听过的新乐器的冲击下,她自然也浸身其中,从上学到做工,每年都追着哼那年晚会的金曲。青梅却在上完初中以后靠着一副莺歌嗓子,报进了市里的戏曲学院。在临走的汽车边,她摇着头问那个小傻蛋,新建的剧团是多,可过些年头,以后没人听戏了,她要怎么办?
“那就到你家白吃吃白喝喝,养我一辈子。”对面的小姑娘轻快地眨眨双眼,把两个人都逗乐了一会儿。可是紧跟其后的,却是急袭过来的虚空与惆怅。等到她提箱上车、坐到车窗边,又探出头来看了看时,两人早已是泪眼婆娑。几年异地传书的青春匆匆而过,好像那天车站里的风轻吹一下,她们就已经各自变成了镇上酒厂的女工人和市剧三团的大花旦,隔着一层台幕互相等待着。
自从天依从戏班毕业,跟着新组建的三团到各处乡下去演出,只要听闻有该团周末在附近巡演的消息,她就会借同学的摩托,披上工资攒的皮夹克,嗡嗡轰轰地骑到开戏的乡镇去,和天依见一面。天依一在台上亮相,眸光一扫,就能看到下边伫盼的阿绫。绫对戏曲全无鉴赏经验,也很难听出名旦和学员的差别来,可只要天依的声音从舞台上亮起来,她就感觉比什么曲子都好听——虽然此时往往伴着身边的骂声:
“直你娘,渠州小百花的质量越改越差了。叫上来的都是什么妖精?大花旦唱断气。”
“你搞不懂。这是小百花三团。”
随着这种说不上是迷信还是醇厚的习俗一道冷却的还有观戏的氛围。自从她一天天长大成人,同辈同学已逐渐不喜欢去看戏。有些人听上了磁带,有些人摇上了天线,厂里也买了吉他,建了兴趣室,一丛小青工爱好在那练谱玩。还有从前中专的男同学同她玩笑,说她从厂里考教师靠夜校,他从厂里考教师就靠吉他——奔着音乐老师去了。
在小时完全没听过的新乐器的冲击下,她自然也浸身其中,从上学到做工,每年都追着哼那年晚会的金曲。青梅却在上完初中以后靠着一副莺歌嗓子,报进了市里的戏曲学院。在临走的汽车边,她摇着头问那个小傻蛋,新建的剧团是多,可过些年头,以后没人听戏了,她要怎么办?

“那就到你家白吃吃白喝喝,养我一辈子。”对面的小姑娘轻快地眨眨双眼,把两个人都逗乐了一会儿。可是紧跟其后的,却是急袭过来的虚空与惆怅。等到她提箱上车、坐到车窗边,又探出头来看了看时,两人早已是泪眼婆娑。几年异地传书的青春匆匆而过,好像那天车站里的风轻吹一下,她们就已经各自变成了镇上酒厂的女工人和市剧三团的大花旦,隔着一层台幕互相等待着。
自从天依从戏班毕业,跟着新组建的三团到各处乡下去演出,只要听闻有该团周末在附近巡演的消息,她就会借同学的摩托,披上工资攒的皮夹克,嗡嗡轰轰地骑到开戏的乡镇去,和天依见一面。天依一在台上亮相,眸光一扫,就能看到下边伫盼的阿绫。绫对戏曲全无鉴赏经验,也很难听出名旦和学员的差别来,可只要天依的声音从舞台上亮起来,她就感觉比什么曲子都好听——虽然此时往往伴着身边的骂声:
“直你娘,渠州小百花的质量越改越差了。叫上来的都是什么妖精?大花旦唱断气。”
“你搞不懂。这是小百花三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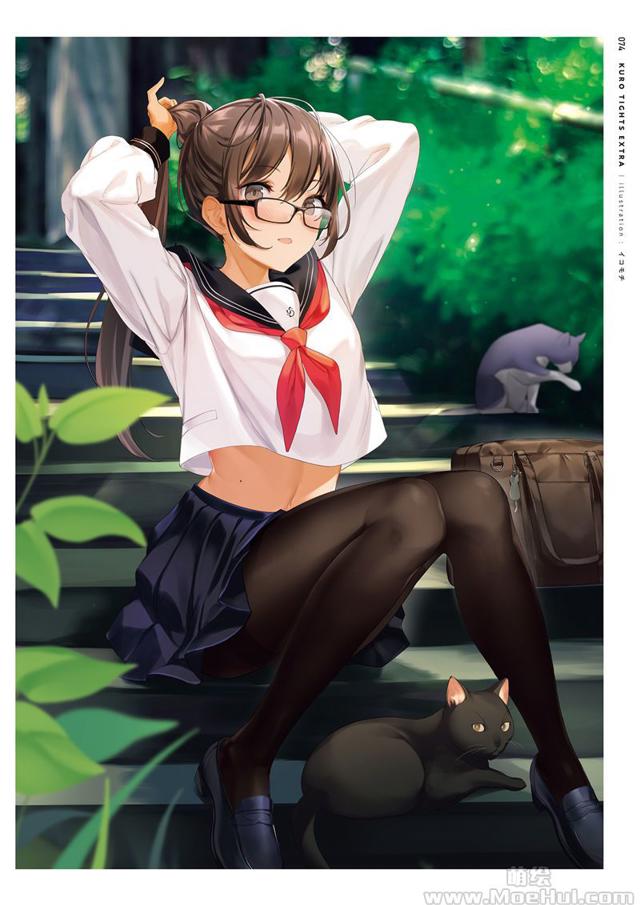
 禁漫夭堂comic北北北砂
禁漫夭堂comic北北北砂














![[南北组]七夕特辑](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306/153019_56697.jpg)
![[南北组]七夕特辑](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731/175846_12080.jpg)
![[南北组]七夕特辑](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904/172051_1483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