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黑塞:中断的课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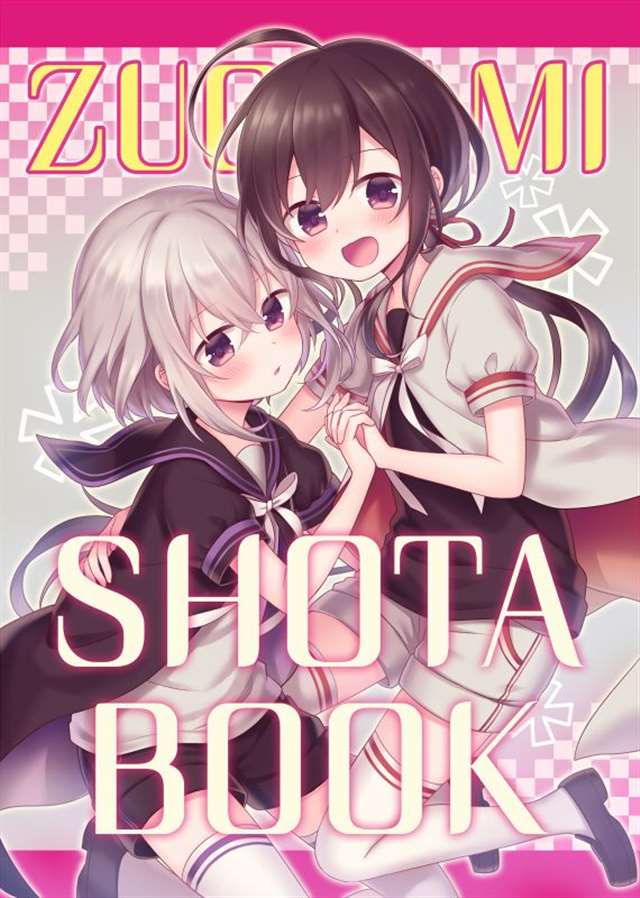
像前辈们那样,看来在今后几年里我必须再次专心致志地回忆孩提时的往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说是种惩罚,还得在相反的前提下,对自己的讲述才能作一番怀疑,并加以弥补。说故事要有听众,讲故事的人要有勇气。你面对的是一群听众,与他们共处一地,其间有个习惯、语言和思维方式的问题,这时你得拿出勇气来。青年时代我崇拜的(至今还爱戴和喜欢的)首先是讲述那个塞尔特维拉故事的叙述大师。好长时间他几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笃信自己和前辈们一样也有这方面的天赋,每次讲故事,也是与我的听众、读者共处一乡的,用他们和我一样既熟悉又认识的乐器和歌谱为他们弹琴吟唱。虽然不像学校用的教科书和儿童看的连环画那样,道理浅显易懂,但在我讲的故事里虽说光明和黑暗,喜悦和悲哀,善良和邪恶,有为和痛苦,有神论和无神论不那么绝对和那么泾渭分明地可以分开来,但其中不乏细腻动人之处,有心理的变化,特别是充满幽默的情趣,什么听不懂,缺乏故事的可述性,什么故事那种展开、冲突、团圆一成不变的清一色情节套路,这些根本性的疑惑一概不存在。
讲故事要像讲塞尔特维拉故事的大师那样讲述;聆听故事要像听大师讲故事那样,给自己和听众带来乐趣。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才慢慢地勉强地认识到自己的生活与讲故事的方式格格不入,为讲故事或多或少占去了大半人生中的阅历,不是放弃讲故事这个行当,就是决定不做一个讲故事的好手,而去做个蹩脚的故事员。从讲述《迪米安》①的故事到介绍《东方之旅》②,我讲的东西越来越脱离美好的传统。假使今天我再尝试写些简短的个人的阅历的话,一切创作技巧都会从我的手中溜掉,亲身的经历几乎像幽灵那样嘈杂、纷繁,难以看透。我不得不承认,近几十年里称得上有分量的有价值的东西莫过于讲述的技巧,但是它已经使我怀疑和犹豫了起来。

 双黑太中中也失忆
双黑太中中也失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