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题

“未花梅树不多山,廊榭沉沉黯旧殷。匹似人才增阅历,少年客气半除删。”
“还阅历,狗蛋儿祺你有甚么阅历?”
“不知喟,小生只顾赏娘娘,驻足延颈不肯离~”
“什么娘娘,你才是娘娘,你,你整个的”
“这是《雀啼》,阿程。”
他说,你一个唱戏的南蛮来东北干嘛?他说你一个搁日本长大的大佐味儿中国人来东北干嘛?那人的眼睛好像给松针扎了一下,没光了。
“日本长大,便要被骂吗?”
马嘉祺把丁程鑫揽过来,那手瘦的好像只有骨没有削去。丁程鑫也瘦,瘦到蝴蝶骨硌得马嘉祺胸口疼。好像飞越海峡的雀精疲力尽地倒在枯枝里。白骨笼着白骨,孤零零的几座黑烟囱前孤零零的树,孤零零里的巢里孤雁啼血。
一滴,在丁程鑫眉间。一滴,在马嘉祺胸口。
“疼吗?”马嘉祺几乎带着濒死的恐慌。丁程鑫从肩头到指尖隔几厘米就开着一朵血花,他看丁程鑫喘气,自己也觉得窒息。丁程鑫点点头,迟疑一下又摆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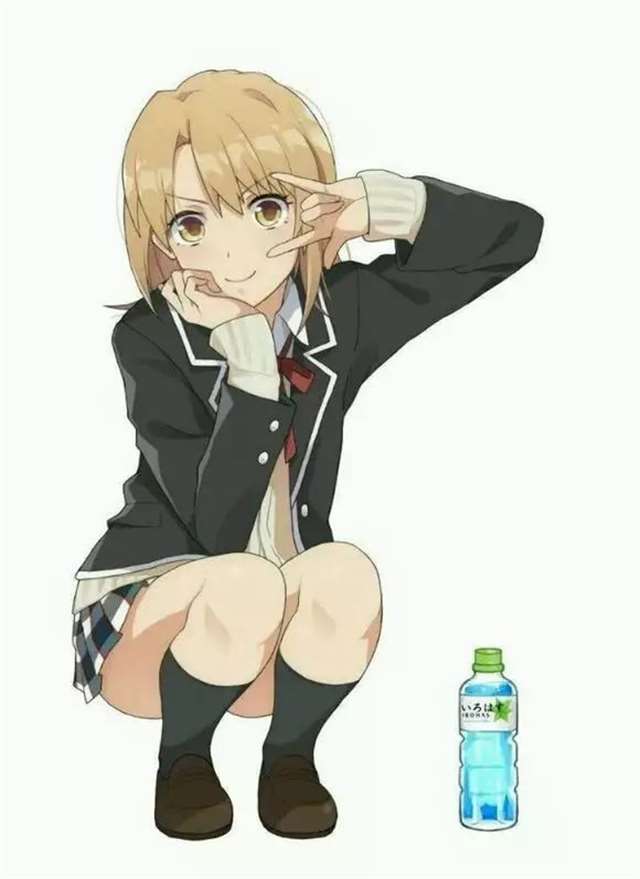
 学长做题错一题
学长做题错一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