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将你坐标变换(上)(23)
“我会的。”
轻歌离开后,余浅唱拨通了阿纳尔的电话。
姜轻歌拉了两个行李箱,背着旅行包和画袋,穿一件印着吉田博水彩画的大号塌肩T恤,独自一人坐电车去了机场。
结束了期末最后一科的考试,我跑出校门等公交车,往常都要等半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此时不到半分钟就到站了。公交车上人还挺多,但恰好空出了一个位置,站着的那些人对座位没有表示兴趣。我坐在座位上,确认了不是谁让给老人的,我把脱下书包抱在胸前。一路上没有几个红灯,一路通畅地到达住院楼。我按了电梯上了九楼,电梯此刻却变得格外得缓慢,好一会儿楼层数才往上跳动一下。我有着一种预感,糟糕的预感。二叔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若是平常他的床头吊瓶架上挂着红细胞悬液,血小板,而我握着颤动的手按下把手进到病房里,二叔的床头的吊瓶架上是一瓶黄色的液体,一瓶白色的液体。17年的时候二叔因为肺部真菌感染住院,我们都以为住个把月就能出来,直到二叔在医院里查出来再生障碍性贫血,我总是以为二叔面色苍白,嘴唇没有血色是他红枣花生汤吃的不够多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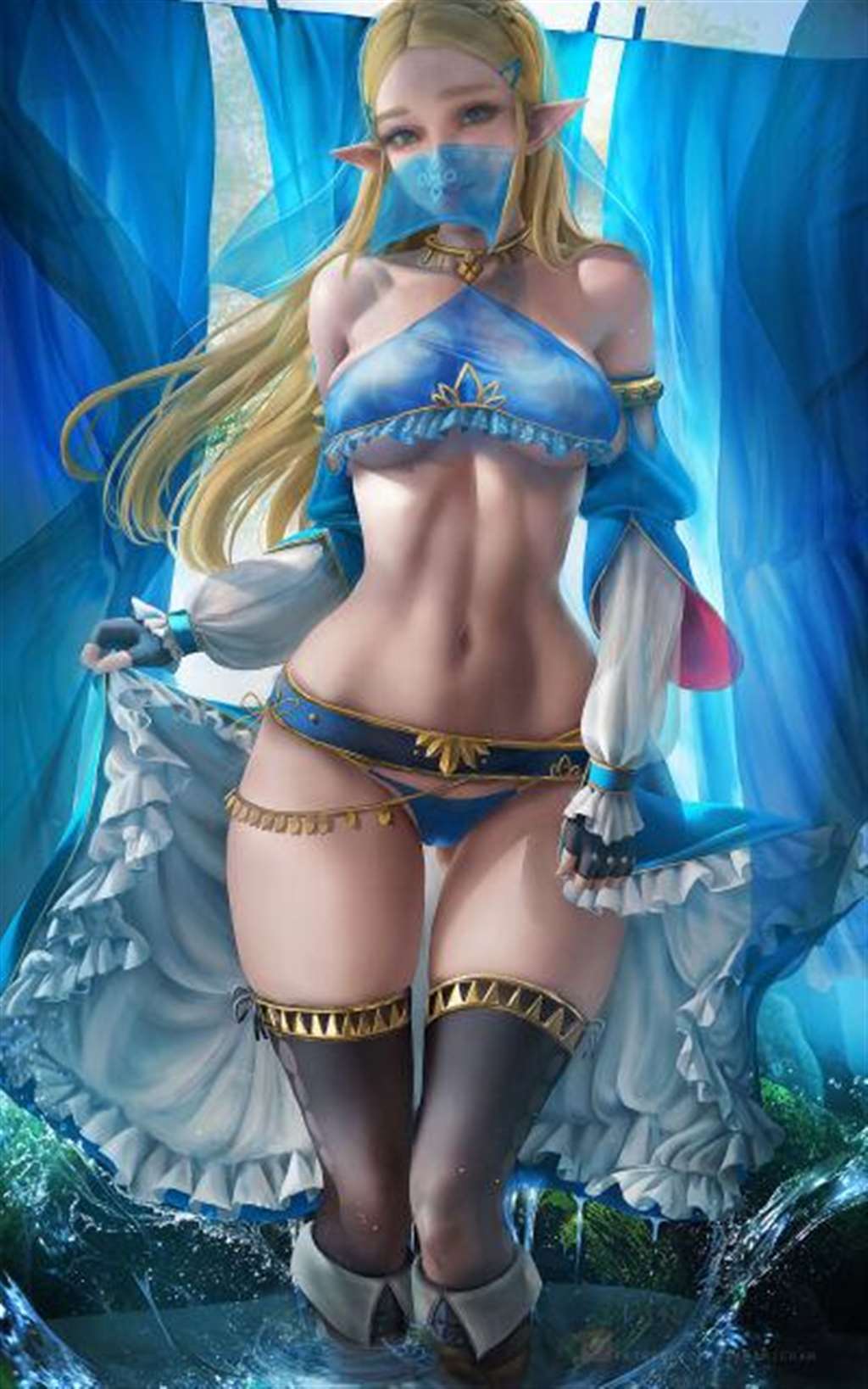
拿了报告后找医生,医生说他这病已经很久了,只是一直没来体检把它查出来,医生拉起二叔的袖子,说这些小红点就是征兆。医生还提起鼻血和牙龈出血,我们确实有印象,可是都以为是二叔油炸食品吃太多的原因。我坐在床边单手握着二叔的手,父母站在床尾,亲戚还没能赶回来。18年1月的时候二叔就转为了重型再障,三姨照顾二叔的那段日子里的一天晚上,二叔内脏大出血直接送入ICU,抢救回来后医院告知我们如果不骨髓移植,内出血只会一次接一次,直至骨髓衰竭。二叔因长期贫血,心脏功能和肝肾功能受损,手术的风险很高,医院开了几次专家会后不敢接,上海的教授来了也说保守治疗,于是一直输血维持治疗。面前的二叔已经白了须发,二叔的脸褶像没有弹性的橡胶,维持着烂泥的坍落状,以前的他笑起来脸就是圆形的,肚子的赘肉总是从衣服的下摆露出来。刚开始治疗的那段时间,二叔的胡子和体毛长得格外的茂盛,二叔说他不想再吃雄性激素了,那玩意让他感觉自己像个野人。

 变物吧变成女生的坐垫
变物吧变成女生的坐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