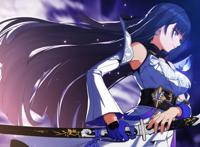旁观者们的独白(下)(6)
怪物的尸体没有任何留下残骸的可能,而尚年轻的老人在几个星期内,都能望见它已经被当场蒸发的证据,那景象深刻在他的记忆里,似乎他终其一生都能望见它,隔着浓稠白色的大气,隔着飞扬的黄沙和绛紫的海水,隔着漆黑的坚硬地面铺展成的的荒芜平原。在他的无限重复的梦境里,硕大蘑菇云的顶端必定高耸地钻出了白雾的上表面,爆炸的震波摇动了大地上全数的古代遗存,向着传说中星尘的方向传送着赤红的万丈焰光。
我只是个科学家,我不知道如何做一个传播者。他无数次在梦里面对父亲这么诉求,呐喊,以至狂吼,痛哭。但当醒来后,在他眼前的就只有漫游车的倾斜的碳素玻璃内壁。平白无故被赋予重任,纵使旁人再怎么义正言辞,当事人自己如何可能不感到彷徨无助?白雾如一张网,牢牢困死他的手脚,使他无法挣脱。
绝望的顶点永远是自暴自弃,并且他实在没有办法抛却前半生用惯的逻辑思维,试图用爵士和士大夫式的,在他眼中则是近乎挣扎的不理智的方式去完成他的使命,然而除此以外,他也别无完成任务的手段。
无法可想,无法可想,途经愤懑,终至绝望。忘了吧,忘了吧。世界终于忘了曾经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屋子,有一座不可思议的核电站。他在延续几十年的旅途中一直有意避开那些偏远地方的不大的屋子,因为他了解那些稳定而闭塞的地方的人的无需言说的排外情绪。他喜欢混迹于大城市的云集的商贾之中,搜集稀奇的见闻,有时亲自去往传说中的地方。他每次都把漫游车藏进远离人烟的隐蔽处,然后乔装成普通的旅人,穿着粗布衣衫步行进入一扇又一扇向上升起的古老的钢铁大门。
他不过是一个异乡人,没有故乡的异乡人。他这么告诉自己。
#9完工后的第七天下午,灯坐在老人的墓碑前。
远处的小山迎着金黄的夕阳,背面的营地的轮廓清晰可见。春夏之交,和煦的风从北方草原来,照例给白雾弥漫的天空染上些微的浅蓝。
老人曾站在山顶上说,他曾经失去作为传承者的使命,有半辈子不知道该干什么。他没有了家,人生像一粒灰尘般满世界飞,无所依傍。“你呢,小伙子?你有自己的责任吗?”灯摇摇头。“那你为什么从自己的故乡跑出来了呢?”
灯说,那不是我的故乡。我只是单纯不想待在那里,仅此而已。老人扭头瞧一瞧他,有一阵沉默不语。
我想逃到哪里去?像老人一样四海为家,抑或是在陌生的城镇作为异乡人定居下来?不,在灯背着小包急匆匆地奔向屋子的暗门时,他的天真的脑瓜对于自己将去向何方是一片空白。与其说他是太过年轻而缺乏经验,毋宁说他似乎对于深思熟虑这件事本身感到一种本能的厌烦,因而甚至在故意放弃思考的机会。想到这里,灯对于自己本身这件东西蓦然感到一丝无端的恐慌,宛如人醒之后面对自己梦游留下的痕迹本能地感到源于未知的恐惧。而诸位看官也不得而知,他这独特的灵魂究竟是各种复杂的因素的怎样的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关于母亲和灶台的记忆缺失了,然而大脑的其他部分明显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未填充完全,而不断产生着不稳定而标志着运转不灵的震颤:我不属于某个地方,但我不知道我属于哪里;这里不是我的故乡,至于故乡究竟是哪里,我也不得而知。
 斗罗大陆独孤雁被独孤博上
斗罗大陆独孤雁被独孤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