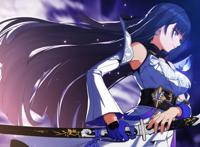旁观者们的独白(下)(2)
冬天“屋外”不下雪,只有像生锈的刀刃般刮着脸。此时城内的供暖系统会毫不费力地将气温维持在舒适的零上五度,刚刚好让人们感受到冬季的气息。家里的电暖炉旁围坐着来闲谈的客人,他们的皮大衣口袋里多数揣着暖身子用的小瓶伏特加。
核电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骄傲。与北方贫瘠草原上的其他城邦不同,他们的“屋子”不需要从定期从墙外弄到可怜的一点点木柴填进炉膛,供暖和供电也不实行配给制。少年的他问电站工作的父亲,我们何以能建起这样奇异的东西?
父亲摸摸自己的络腮胡,眼镜下面闪过一道奇异的光:“这当然不是现在的人能造出来的,我们和其他地方的人没有什么知识方面的差别。“
今人做不到的事,古人却能做到么?用木舟和木桨,何以能航遍西南太平洋?用绳索和斜面,何以能建起金字塔?原子弹又是如何炼制的呢?计算机芯片又是如何刻蚀的呢?人类何时进取?何时忘却?何时对于宇宙之深邃无垠感到无能为力而畏首畏尾,又何时为了达成伟大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地前行?他曾无数次坐在厂房的楼顶边缘,面对反应堆拱起的半球形外壳在屋顶日光灯下映出的剪影长久地发呆,没头没尾地想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春夏之交时从北方草原来的含有水汽的微风有时能够稍稍驱散白雾,从气密门出去的远行的贸易人便会隐约地看到南边的沙漠里有一座山一般高耸入云的古代建筑。建筑整体呈四方的高耸塔状,顶端有一个尖锐的结构。那高塔是这个屋子的标志物之一,一个没人知道哪朝哪代建造的祭坛的边缘区域的最高建筑。他知道那里只有大片的水泥地面,作为大殿残余的大块方形地基,而那最高的建筑本身似乎完全是由性质近乎不可思议的古代钢材所建造。即使表面涂刷的油漆早已只剩痕迹,所有的钢板仍然完好地在它们原本的位置上构成一个非凡的工程整体,严整的结构似乎在反衬这世界的其余每样东西的脆弱易碎。
他有时觉得那古塔同核电站一样,拥有某种奇异而不可名状的本质,它们仿佛不属于这干燥的内陆地区,而与画册上看到过的古时候的海岸地区给人的感觉更加相似。在它们诞生的那个年代世界一定没有这漫天的风沙,人们抬头就能看到无限深远的天空,他们一定有机会长时间地盯着它,在为吃饱穿暖而忙活的间隙做无尽的畅想,想着天外是否还会有另一个大地,想着他们某一天可以在自己的背上装上木质的翅膀,飞得比所有迁徙的候鸟更高,一直飞到传说中金光熠熠的太阳的旁边。
半个多世纪以后,在土坯砌成的实验室里,未来的老人将会一次次回忆起这许多自己十二岁那年夏天之前常有的洋洋洒洒的不着边际的念想。那时他开始上为未来的核电站操作人员专门设立的高级学校,准备有朝一日子承父业。生活似乎仍将继续,时间将如同平坦的大道般一往无前直到生命尽头。几个月后他从新认识的学校历史老师口中得知这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那个祭坛真正的“名字”,即古人称呼它的最初发音,似乎为“拜科努尔*”。
 斗罗大陆独孤雁被独孤博上
斗罗大陆独孤雁被独孤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