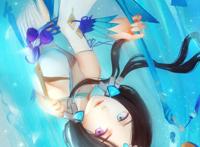被劈成两半的子爵(9)
“在这两个半边之中,好人比恶人更糟。”在泰拉尔巴,已经有人这么说了。
恶人听到了好人的讯踪,大为恼火,这败坏了他作恶的形象。“看着吧,我定要搅黄他。”恶人收起自己的斗篷,在月夜下撑起满天银辉。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
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花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人们惊奇的发现被好人管控的生活正因为恶人的参与而有了起色——恶人所及之处,到处都是酣畅淋漓的破坏,也到处都留下纵情声色的引诱与对好人不加掩饰的嘲讽:
“你个肺痨鬼”
“你是不是被盐堵了耳朵,一张嘴便是咸的?”
“鄙人愿成为你喉咙下的枪魂。”好人总是这么答到。
心怀恶意的人没有一个月夜不是恶念丛生,像一窝毒蛇盘绕于心间;而心地慈善的人也不会产生出放弃私念和向他人奉献的心愿,像百合花一样开放在心头。梅达尔多的两个半身正是如此,他们忍受着完全相反的痛苦与煎熬,月夜里在泰拉尔巴的山崖上打滚,但是讽刺的是,那被他们震慑的完人们,枕着自己的麦秆沉沉睡去,在黎明的破晓中毫不在乎。
当帕梅拉要出嫁时,整个泰拉尔巴都轰动了,城堡里正张灯结彩,准备盛典,子爵忙得把黑绒衣裤的袖子和裤褪上各磨了一个大破洞,而流浪汉也洗刷了那匹可怜的骡子,缝补了衣服的肘拐处和膝盖头。教堂也点燃了蜡烛,两边有条不紊,相得益彰。
“你将嫁给哪一个呀,帕梅拉?”我问她,“我不知道,”她回答,“我真不知是好是坏。”
不一会儿,从森林里传来喉咙大喊声,一会儿又传出长吁短叹声。原来是那两位半身郎沉浸在结婚前夕的兴奋中在山间漫步,彼此不得而知。他们都披着黑色斗篷,一个骑着瘦马,一个骑着骡子,都陶醉于热切的幻想中不能自持了,不是仰天长啸就是低首叹息。马走沟壑悬崖,骡走山坡高低,骑者不曾碰面。
恶人听到了好人的讯踪,大为恼火,这败坏了他作恶的形象。“看着吧,我定要搅黄他。”恶人收起自己的斗篷,在月夜下撑起满天银辉。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
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花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人们惊奇的发现被好人管控的生活正因为恶人的参与而有了起色——恶人所及之处,到处都是酣畅淋漓的破坏,也到处都留下纵情声色的引诱与对好人不加掩饰的嘲讽:

“你个肺痨鬼”
“你是不是被盐堵了耳朵,一张嘴便是咸的?”
“鄙人愿成为你喉咙下的枪魂。”好人总是这么答到。
心怀恶意的人没有一个月夜不是恶念丛生,像一窝毒蛇盘绕于心间;而心地慈善的人也不会产生出放弃私念和向他人奉献的心愿,像百合花一样开放在心头。梅达尔多的两个半身正是如此,他们忍受着完全相反的痛苦与煎熬,月夜里在泰拉尔巴的山崖上打滚,但是讽刺的是,那被他们震慑的完人们,枕着自己的麦秆沉沉睡去,在黎明的破晓中毫不在乎。
当帕梅拉要出嫁时,整个泰拉尔巴都轰动了,城堡里正张灯结彩,准备盛典,子爵忙得把黑绒衣裤的袖子和裤褪上各磨了一个大破洞,而流浪汉也洗刷了那匹可怜的骡子,缝补了衣服的肘拐处和膝盖头。教堂也点燃了蜡烛,两边有条不紊,相得益彰。
“你将嫁给哪一个呀,帕梅拉?”我问她,“我不知道,”她回答,“我真不知是好是坏。”
不一会儿,从森林里传来喉咙大喊声,一会儿又传出长吁短叹声。原来是那两位半身郎沉浸在结婚前夕的兴奋中在山间漫步,彼此不得而知。他们都披着黑色斗篷,一个骑着瘦马,一个骑着骡子,都陶醉于热切的幻想中不能自持了,不是仰天长啸就是低首叹息。马走沟壑悬崖,骡走山坡高低,骑者不曾碰面。

 岳母半推半就的同意了
岳母半推半就的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