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茶厝【南北组国庆24h】(5)
我不知她在此地租住哪里,姓甚名谁,不来时平日做什么,奔波他地又做什么,她不说,只说闲话,我也不想过问,只问她茶水是不是好喝,她那天二更牵马来,我说,闽南熟茶,暖胃提神,你身上多伤,喝茶好,熬夜不好。
她说老板娘漂染的银发皎如三更的满月,好看的,卿有双鬓生两翼,皎如鹭鸶飘如蝶。
她问我你去没去过北方和江南,江南春三月江水青绿如玉,杏桃李梨渐次绽开,人于花海酣眠,有海棠瓣落在发丝间,风扫不尽,六月梅雨,房屋抽缩成一团湿软土糊;跨过淮河就是干燥松弛的黄土,高原平原,土丘上有会落叶的细瘦小树,冬天大雪结冰冻裂河道,夏天有骄阳烤干头顶,洛阳城里马蹄扫起飞沙,古城墙残垣上有终年不化的积雪。她说我很多年前辞官出京都,是在冬至,五更鼓提灯出府,马车卷在大雪里,揉捻得矮小狼狈。
屋外微雨,我送客闭门,起锅炒茶,偏头看她说,我去过的。年少时喜云游,要奔波度日,不背行囊,过江、渡海,北上、南下。中原的大雪,太大了,撒盐空中不可拟;南洋天热,纱薄,多矿,我的纱衣裙与锡制茶具多是多年前乘福船过南海买的,还有内屋的南洋瓷砖。现在不去了,只有这些,所以不卖。
我继续说,我曾身背茶袋,沿关中土路驾木板车直下,穿白衣,土壤松弛不平,一路颠簸,车轮搅打黄沙,风舞尘沙拍向面目衣裙,白裙沾上捣洗不净的沙粒。我想奔波辛苦,我的家乡没有尘土。
回乡后洗净长发,它变成银丝,于是我此后定居,开茶馆,也有六七年。
我记得那时我回头远眺已行的路,风沙填平车痕,抓提我的发丝。
她抓起一把叶撒在锅子里。我说不愧是练武的,好准。她说,行了,我来炒。
她拿起大勺炒茶,我倚在墙上抽她剩下的烟。她回头说,我来时带着一把戟枪尖,青铜做的,骑马破阵,枪尖闪着熠熠金光。后来我拔下枪尖,背在行囊里辗转许多下雨的地方,渡过南海,它缓慢生长许多层绿锈,恰如泡在软泥中的乌木历经多年,青苔发育,滋生的周期跃出时间的长轴。它表层脆软,一碰就碎,我想能卖个江湖郎中拿去入药。
我点头上前,将烟气吐在她后颈,褪下她的纱袍,一路吻她愈合结痂的豁口,脊椎到腰腹,箭孔或刀口,紫红色的痂,深的,长的。我听见她微弱的喘息,她握勺的手在颤,我把住她的手,继续翻炒茶叶。
她说老板娘漂染的银发皎如三更的满月,好看的,卿有双鬓生两翼,皎如鹭鸶飘如蝶。
她问我你去没去过北方和江南,江南春三月江水青绿如玉,杏桃李梨渐次绽开,人于花海酣眠,有海棠瓣落在发丝间,风扫不尽,六月梅雨,房屋抽缩成一团湿软土糊;跨过淮河就是干燥松弛的黄土,高原平原,土丘上有会落叶的细瘦小树,冬天大雪结冰冻裂河道,夏天有骄阳烤干头顶,洛阳城里马蹄扫起飞沙,古城墙残垣上有终年不化的积雪。她说我很多年前辞官出京都,是在冬至,五更鼓提灯出府,马车卷在大雪里,揉捻得矮小狼狈。
屋外微雨,我送客闭门,起锅炒茶,偏头看她说,我去过的。年少时喜云游,要奔波度日,不背行囊,过江、渡海,北上、南下。中原的大雪,太大了,撒盐空中不可拟;南洋天热,纱薄,多矿,我的纱衣裙与锡制茶具多是多年前乘福船过南海买的,还有内屋的南洋瓷砖。现在不去了,只有这些,所以不卖。

我继续说,我曾身背茶袋,沿关中土路驾木板车直下,穿白衣,土壤松弛不平,一路颠簸,车轮搅打黄沙,风舞尘沙拍向面目衣裙,白裙沾上捣洗不净的沙粒。我想奔波辛苦,我的家乡没有尘土。
回乡后洗净长发,它变成银丝,于是我此后定居,开茶馆,也有六七年。
我记得那时我回头远眺已行的路,风沙填平车痕,抓提我的发丝。
她抓起一把叶撒在锅子里。我说不愧是练武的,好准。她说,行了,我来炒。
她拿起大勺炒茶,我倚在墙上抽她剩下的烟。她回头说,我来时带着一把戟枪尖,青铜做的,骑马破阵,枪尖闪着熠熠金光。后来我拔下枪尖,背在行囊里辗转许多下雨的地方,渡过南海,它缓慢生长许多层绿锈,恰如泡在软泥中的乌木历经多年,青苔发育,滋生的周期跃出时间的长轴。它表层脆软,一碰就碎,我想能卖个江湖郎中拿去入药。
我点头上前,将烟气吐在她后颈,褪下她的纱袍,一路吻她愈合结痂的豁口,脊椎到腰腹,箭孔或刀口,紫红色的痂,深的,长的。我听见她微弱的喘息,她握勺的手在颤,我把住她的手,继续翻炒茶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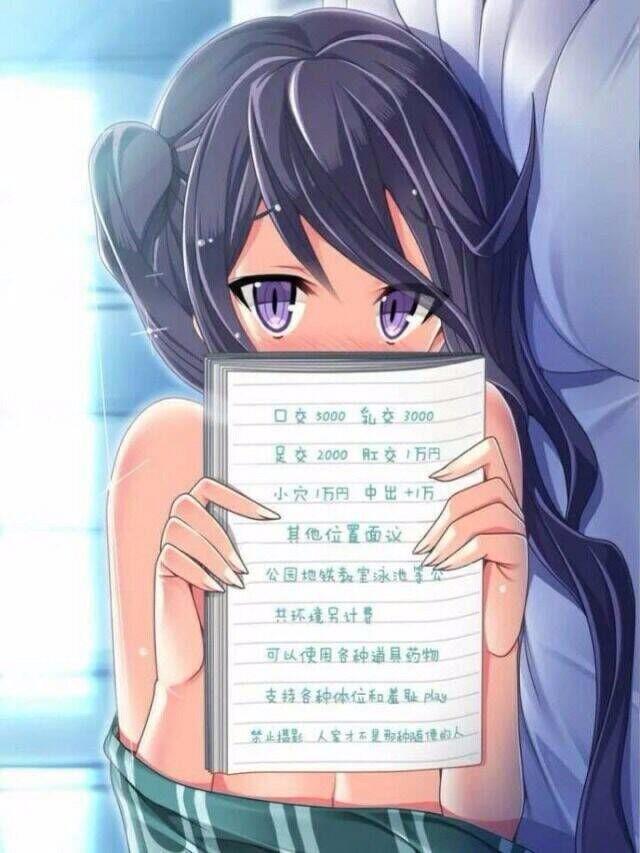
 禁漫夭堂comic北北北砂
禁漫夭堂comic北北北砂

























![[8:00]糖[南北组国庆24h]](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408/151220_12833.jpg)
![[8:00]糖[南北组国庆24h]](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408/152418_51883.jpg)
![[8:00]糖[南北组国庆24h]](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408/154244_30010.jpg)
![[8:00]糖[南北组国庆24h]](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613/174811_3777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