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莎】 如果玻璃犀牛只爱自己(9)
系里曾经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这份申请的前途,每个人都不止一次地给它判过死刑。可仍然是在写。联名也总是都签,但结局总是不如人意。其实签名也不过就是写几个字,尽管现在大家对写下自己的名字更谨慎了。
“如果申请下来,你是大功臣。”
系主任天天这么骗人。估计他自己也觉得神奇吧,居然每次这么说都有人信。不过他说的话也确实大多人都信。但是我们几乎没有聊过有关话题,因为想写就写,不想写就拉倒。这是一种没来由的神经病,没有硬性规定,也许是体育部椅子的诅咒。
“写生?采风?”
“都好啊。反正以后干什么都有用……”
我蹭了蹭鼻子:“你什么时候去一趟?
“谁想去就能去啊?”
“成绩好就能去。——开玩笑。”
“真没意思啊。”
我佯怒:“你说谁呢你?”
诸如此类的交流越来越少。近一年我们特别疏远且温和起来,不完全是我搬到老校区上学的原因。一年前我们有一次一起代表系里出国交流,建立起一些若有似无的友情,若有似无到我们以为是彼此的错觉。老校区在市中心,哪里都离得很近;新校区在市郊,去哪儿都是跋山涉水。我跟她说过有时间到城里(我跟每个朋友都说过),有什么事儿找我都行。前几天却是我们一年来第一次通电话,不算打错的。我看不到她,她也看不见我。估计她也觉得离谱吧,一年到头在新校区见不到两次,这么几天见了三次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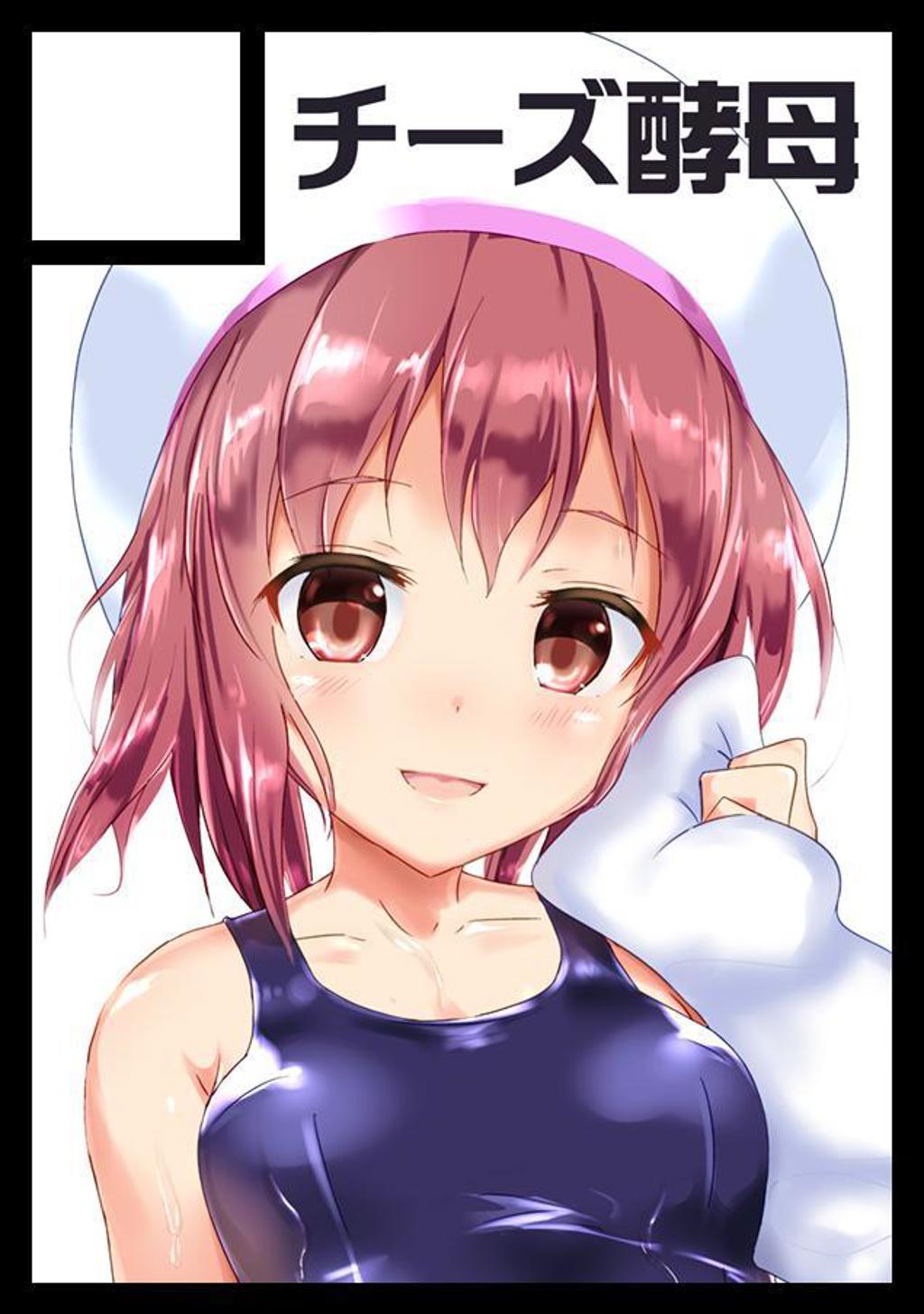
“我看你不是挺闲的?”
“不在学校,不看汇报。”
气得她吹胡子瞪眼。我们穿过一片梧桐树林,早在盛夏地上就落满了叶子。我拎着书本的一角,晃来晃去,摇摇欲坠。我们走到表导楼底下,看到一对情侣分别站在学校大门内外对山歌。我们俩内心擦汗——总之走了一段路,必须要在这里分手。
我有一个真正好奇的问题,但在看到那对情侣的时候就完全忘了,直到钱天一从表导楼冲出来报告前线战况时我也没想起来。
“不好啦——咱们教室又被别的系占啦——”
她就差手上有把刀拔出来冲上楼去,但是她没有刀,只能拍拍钱天一的肩,“走,我就不信今天弄不——”走了两步又回头喊,“等你回来!”
“干啥呀,帮你打架啊?”
“打架不用你,但不看我们汇报你真的亏了。”
她把她的汇报描述得惊为天人后,拉着钱天一跑了,准备拳打脚踢外系人去了。
“你好像个票贩子……”
我喊了一句,看了一会儿上下翻飞乱蓬蓬的头发,转头摸出学生卡走到大门边。

 把我按在在落地玻璃窗前做gh
把我按在在落地玻璃窗前做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