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一)(2)
这是他的成名之作,是在他年轻时写就的。故事要从一九三零年讲起,那时他不到二十一岁,刚刚勉强完成了在大学的课业,来到大城市里讨生活,每天忍饥挨饿,最大的担心便是自己吃不饱。刚从学校出来,仍未摆脱那股天真的书卷气,就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局面,城市里的烟火也异常寥落,失业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排成长队向着领取救济粮的地方游荡,盼着去那里领一块面包吃,混迹在队伍里,他总是低下头,不愿去看旁人的眼睛。
一边辛苦维生,一边偿还贷款,种种新鲜事,他不愿对家里人说。他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都是世代耕作的农民,扎根于阿拉巴马的乡下,以为所遭遇的一切都是源自上帝,而不是某些扮演上帝的家伙。他们送他读到大学,只是把这当作他的命运,就像曾和他们一起在田里劳作的牲口一样,并未对此讲过什么道理。他那时根本不知道,怎样把自己在城市里遭遇的事情对他们讲清楚,现在想起来依然如此。而后每当他抚摸着二人瘦小的墓碑,也只能苦笑几声,“感谢上帝”。
他干过工人,干过服务员,给报社跑过腿,给旅店做过勤杂工,给达官贵人们做过马夫和球童,甚至充当过地下拳市的裁判,可以说一切能够出卖力气的行业,他都尝试过了。每日的薪水少得可怜,可市民们还时常举行罢工游行,这更让他饥肠辘辘,迫不得已,他被人领着加入了某个工会组织,混迹在人声鼎沸的旗帜和标语里,跟着大家讨一口饭吃——后来他才逐步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对于政治,他一点也不关心,但环顾四周,似乎这是能让他混到饭票的唯一话题。取代了那些都市传说,家长里短,明星绯闻和刑事案件,每个人都在谈论民族、国家、世界的未来,谈论那些他们共同的敌人,谈论人类的伟大和他们的历史使命,谈论那些躲在幕后的家伙们。
他加入进来,起初只是小心地观望,生怕犯错而被打成敌人,听着那些高谈阔论者的辞令,学着他们的腔调做事,企图从中找到些规律来。
起初他在工会做着派发传单,打杂跑腿的零散活计,像个沉默的木偶人,别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直到有天,有个表情激愤的家伙跑过来,拿着手里墨迹未干的稿子对他说:
“你得说话,明白吗?向这狗娘养的世界发出你的声音!”
勒夫仿佛听到了总统的命令似的,一下子醒过来。他开始撰写些标语,简单的告示,报纸上的笑话之类,觉得体内某种淤积多年的东西慢慢被排出去了,但随即又有什么东西钻了进来。一开始,他实在不知道写些什么,仅凭着学校图书馆里那些断断续续的文学知识凑出些句子,以致于写完之后,他盯着那些古怪的字母,好像学会了一门新的语言。
他写的标语,即使在最人迹罕至的街区,也会让孩子们发出傻乎乎的笑声,可给报社来电的读者们又纷纷说他没有幽默感,写出的笑话让人牙齿打颤。
一边辛苦维生,一边偿还贷款,种种新鲜事,他不愿对家里人说。他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都是世代耕作的农民,扎根于阿拉巴马的乡下,以为所遭遇的一切都是源自上帝,而不是某些扮演上帝的家伙。他们送他读到大学,只是把这当作他的命运,就像曾和他们一起在田里劳作的牲口一样,并未对此讲过什么道理。他那时根本不知道,怎样把自己在城市里遭遇的事情对他们讲清楚,现在想起来依然如此。而后每当他抚摸着二人瘦小的墓碑,也只能苦笑几声,“感谢上帝”。
他干过工人,干过服务员,给报社跑过腿,给旅店做过勤杂工,给达官贵人们做过马夫和球童,甚至充当过地下拳市的裁判,可以说一切能够出卖力气的行业,他都尝试过了。每日的薪水少得可怜,可市民们还时常举行罢工游行,这更让他饥肠辘辘,迫不得已,他被人领着加入了某个工会组织,混迹在人声鼎沸的旗帜和标语里,跟着大家讨一口饭吃——后来他才逐步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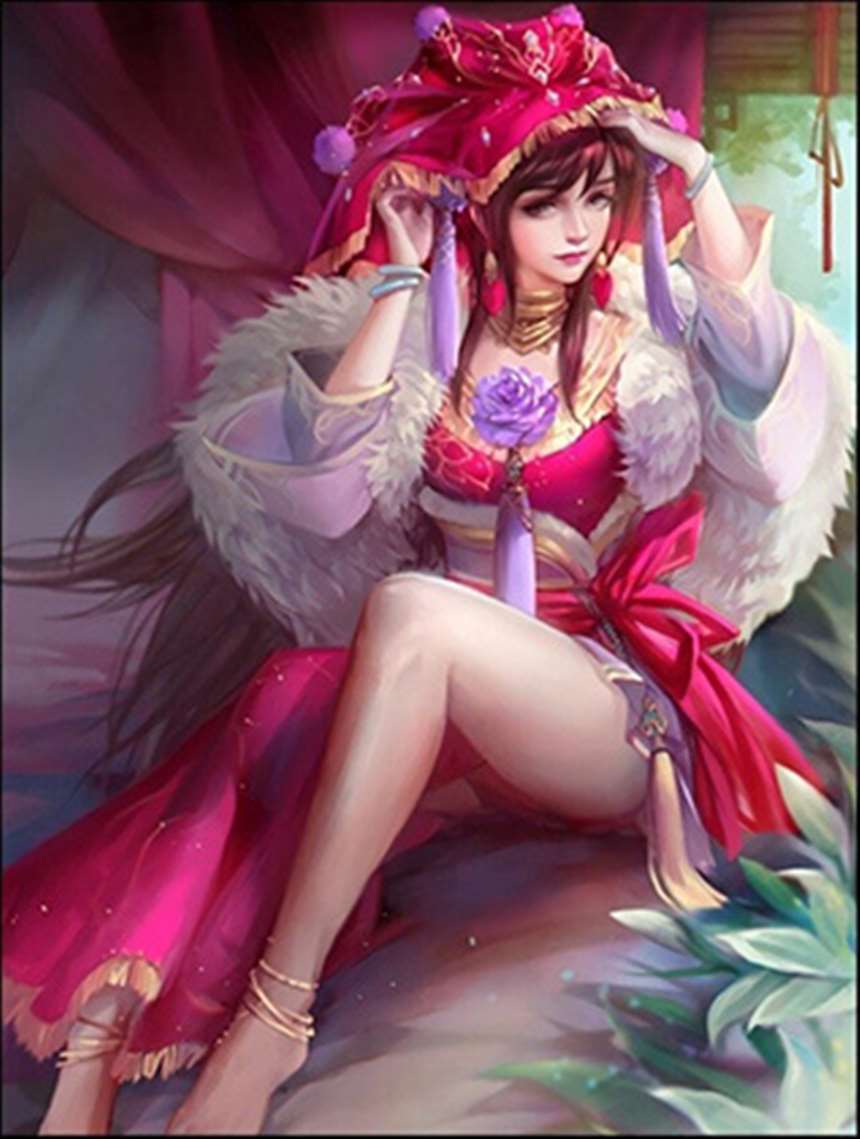
对于政治,他一点也不关心,但环顾四周,似乎这是能让他混到饭票的唯一话题。取代了那些都市传说,家长里短,明星绯闻和刑事案件,每个人都在谈论民族、国家、世界的未来,谈论那些他们共同的敌人,谈论人类的伟大和他们的历史使命,谈论那些躲在幕后的家伙们。
他加入进来,起初只是小心地观望,生怕犯错而被打成敌人,听着那些高谈阔论者的辞令,学着他们的腔调做事,企图从中找到些规律来。
起初他在工会做着派发传单,打杂跑腿的零散活计,像个沉默的木偶人,别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直到有天,有个表情激愤的家伙跑过来,拿着手里墨迹未干的稿子对他说:
“你得说话,明白吗?向这狗娘养的世界发出你的声音!”
勒夫仿佛听到了总统的命令似的,一下子醒过来。他开始撰写些标语,简单的告示,报纸上的笑话之类,觉得体内某种淤积多年的东西慢慢被排出去了,但随即又有什么东西钻了进来。一开始,他实在不知道写些什么,仅凭着学校图书馆里那些断断续续的文学知识凑出些句子,以致于写完之后,他盯着那些古怪的字母,好像学会了一门新的语言。
他写的标语,即使在最人迹罕至的街区,也会让孩子们发出傻乎乎的笑声,可给报社来电的读者们又纷纷说他没有幽默感,写出的笑话让人牙齿打颤。

 佟年韩商言怀孕去医院
佟年韩商言怀孕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