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遥远星辰归来的故人(4)
“舍不得火星?”阿荧问道,他很少在专业问题以外的地方对他发问——或许也曾经问过,只是上校不怎么记得了。
“有点。”上校的回答很简练,却是难得对人的真诚。哪怕早就知道这个项目终将失败,在得知项目无限期中止的时候仍有难以言说的失落。他在这里付出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也是一份事业,甚至——一份目标。
“很少有能让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目标了。”或许在深空待得久了容易变成一个国际主义者,在出一点分毫的差错就会丧命的环境中时,人与人之间比起生存竞争,更多的是一种共同面对宇宙和自然的共生关系。
因此,当得知阿荧努力把所有语言、肤色各异的被各国所抛弃的移民也聚集在一起准备一起踏上返回地球之旅时,他对于这个小青年的看法也不禁改善了许多。
“我还以为像您这样的人不会抱有这种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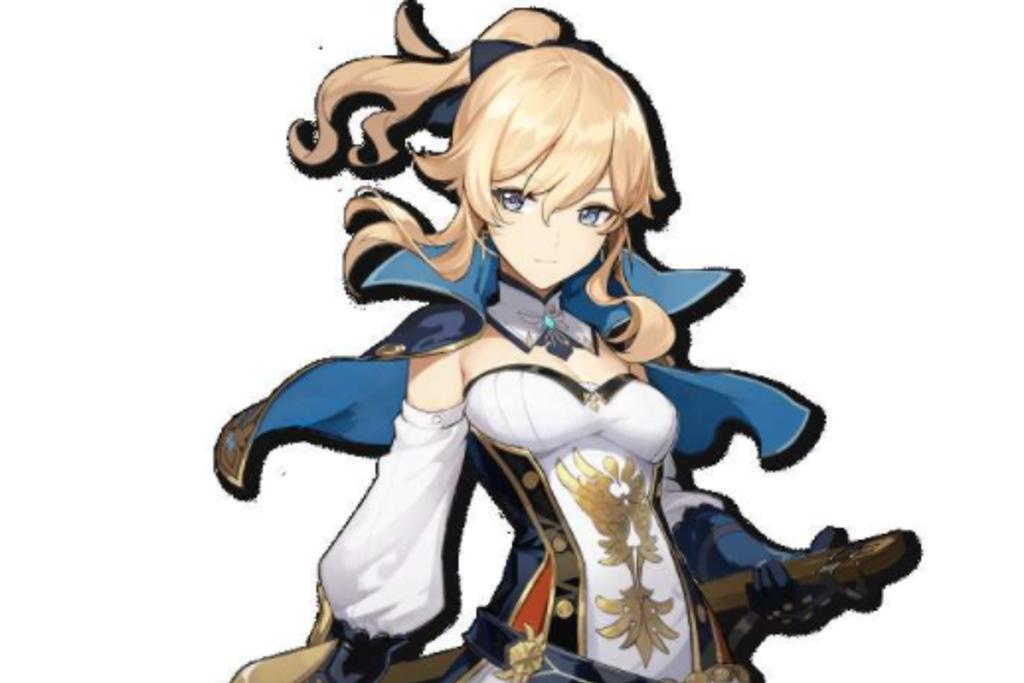
“你是说幼稚病?”
“我是说理想主义。”阿荧说道,上校这时候才会仔细端详这个年轻人的脸,深重的黑眼圈和惨白的脸色之下有一股令他感到有些亲切的书生意气,就像他的技术团队里许多年轻人一样,会为了一个课题而茶饭不思绞尽脑汁。
或许自己对于后生不该这么严苛?上校第一次开始这样反思自己。
“你倒是走的坦荡,”上校道,“你不是在这火星上出生的么?原以为你应该会更舍不得才是。你那太空中进行的栽培,回到了地球可就只能停留在实验室里了。”
“舍不得是有的,但事已至此已经只能接受而已。”阿荧的回答却非常微妙,“有时候我在想或许我们这个族群还没有到可以进行太空开拓的时候——我不单是指基础自然科学和技术上的不成熟,还有社会学意义上的不成熟。生活在蓝星上不同的社群不说通力合作,至少能做到不再彼此掣肘……”
“这比搞技术难。”
“就像核可以提供高效清洁的能源、也能轻易的毁灭到我们这个族群一样,但能决定它被如何使用的从来就不是我们这些搞技术的人,我们创造着描绘历史的纸笔,但绘画的另有其人”上校用手势示意他可以随便找个椅子坐下,阿荧则恭恭敬敬的坐在了上校正对面的一张椅子上,“我的运气还算好,至少我研究的玩意儿很难被用在非正义的目的上。”

 蓝湛故意让魏无羡看到自己的那个
蓝湛故意让魏无羡看到自己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