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雪(7)
阿文见他笑着,便也强笑,只是笑容仍然苦涩:“你以前面对的南国藩镇,无论是马殷还是杨行密,都不过是守家之犬,不足为虑。胡虏却不同,李存勖穷凶极恶,绝非南国诸藩可比,你万万要小心。”
他不再多言,只是从阿文手中接过酒,一樽缓缓入喉,然后举起空樽高呼:“臣刘隐,祝大梁江山寿!”
三位皇子齐齐作揖:“南国之主威武!”
抵达前线时,已是满天飞雪。朔风凛冽,战鼓骤然,他打了个寒噤,然后轻轻拂衣,便抖落了半身霜雪。
沙陀人的军营就在前方,隔着遥遥的雪原,已是肉眼可见。朝廷有限的兵力已调往凤翔抵抗李茂贞,沙陀人将全部由南国大军对抗。
王审知惊叹:“北国的雪,的确比南国霸道。”
郑买嗣忧虑:“沙陀人军威雄壮,显然是精锐,此行确实棘手。”
高季兴最是洒脱:“李存勖也是一个脖子一个脑袋,怕他做甚!”
他忍不住又咳了几声,待缓过气来,便说:“吩咐下去,出击,杀胡虏!”
战事进行的异常艰难,北国胡骑悍勇迅捷,又占据地利;南国精锐胜在装备精良,斗志昂扬。两军鏖战许久,互不能胜。
一个胡人登上战车,朝着战场高呼:“我是李存勖,南国之主,何不一叙?”
他亦登上战车,与李存勖遥遥相望,神情冰冷。朔风如刺,透过他的皮肤,刮着他的骨骼,刮得他脸颊毫无血色。
李存勖笑着说:“你我一南一北,万里之遥,素来秋毫无犯,你又何必来伐我?”
他平静地说:“泱泱华夏,还轮不到异族染指。你就此退去,此事便作罢。”
李存勖轻轻摇头,说:“朱温篡唐窃国,倒行逆施,朱家江山气数已尽,你又何必逆天而行!汉人主宰天下数百年,也是时候换我族来为至尊了。”
他说:“梁唐之争乃我汉人内务,何须沙陀人来嚼口舌?”
李存勖又说:“你我何不联手荡尽不臣,然后划江而治,双分天下。我们沙陀人取北国便可,南国仍归你们汉人。”
他转身离开战车,对等候在旁的各路将领吩咐:“继续战吧,战到胡虏退却,或是汉家儿郎死绝。”
又打了半个月,两军都是损失惨重,沙陀人终于坚持不住,率先退兵。他屹立在前线望着退走的胡人,狰狞的甲胄也掩盖不住他愈发嶙峋的身子,宛若一颗瘦竹。
李存勖随着大军退去,不时回过头看他,冷笑着说:“听说你早年在韶州受过重伤,落下病根,看来是真的。你这病秧子恐怕没几年好活了,等你死掉,我还会回来的。到了那时,且看还有谁敢拦我!”
他不再多言,只是从阿文手中接过酒,一樽缓缓入喉,然后举起空樽高呼:“臣刘隐,祝大梁江山寿!”
三位皇子齐齐作揖:“南国之主威武!”
抵达前线时,已是满天飞雪。朔风凛冽,战鼓骤然,他打了个寒噤,然后轻轻拂衣,便抖落了半身霜雪。
沙陀人的军营就在前方,隔着遥遥的雪原,已是肉眼可见。朝廷有限的兵力已调往凤翔抵抗李茂贞,沙陀人将全部由南国大军对抗。
王审知惊叹:“北国的雪,的确比南国霸道。”
郑买嗣忧虑:“沙陀人军威雄壮,显然是精锐,此行确实棘手。”
高季兴最是洒脱:“李存勖也是一个脖子一个脑袋,怕他做甚!”
他忍不住又咳了几声,待缓过气来,便说:“吩咐下去,出击,杀胡虏!”
战事进行的异常艰难,北国胡骑悍勇迅捷,又占据地利;南国精锐胜在装备精良,斗志昂扬。两军鏖战许久,互不能胜。
一个胡人登上战车,朝着战场高呼:“我是李存勖,南国之主,何不一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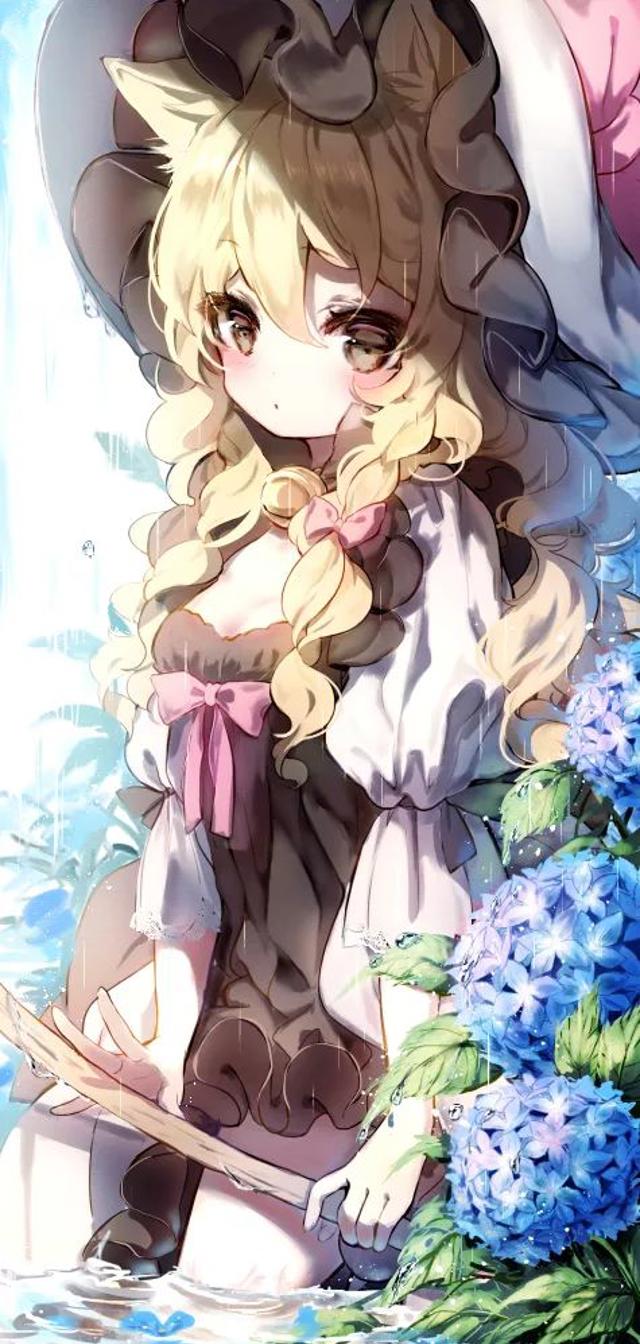
他亦登上战车,与李存勖遥遥相望,神情冰冷。朔风如刺,透过他的皮肤,刮着他的骨骼,刮得他脸颊毫无血色。
李存勖笑着说:“你我一南一北,万里之遥,素来秋毫无犯,你又何必来伐我?”
他平静地说:“泱泱华夏,还轮不到异族染指。你就此退去,此事便作罢。”
李存勖轻轻摇头,说:“朱温篡唐窃国,倒行逆施,朱家江山气数已尽,你又何必逆天而行!汉人主宰天下数百年,也是时候换我族来为至尊了。”
他说:“梁唐之争乃我汉人内务,何须沙陀人来嚼口舌?”
李存勖又说:“你我何不联手荡尽不臣,然后划江而治,双分天下。我们沙陀人取北国便可,南国仍归你们汉人。”
他转身离开战车,对等候在旁的各路将领吩咐:“继续战吧,战到胡虏退却,或是汉家儿郎死绝。”
又打了半个月,两军都是损失惨重,沙陀人终于坚持不住,率先退兵。他屹立在前线望着退走的胡人,狰狞的甲胄也掩盖不住他愈发嶙峋的身子,宛若一颗瘦竹。
李存勖随着大军退去,不时回过头看他,冷笑着说:“听说你早年在韶州受过重伤,落下病根,看来是真的。你这病秧子恐怕没几年好活了,等你死掉,我还会回来的。到了那时,且看还有谁敢拦我!”

 火影小南怀孕训练漫画
火影小南怀孕训练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