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的乡愁是血泪在沉淀:男人不哭,只是未到伤心处(3)
文中写到,他的声音还带着“浓浊的川腔”,可见多年来他虽身居台北却始终乡音不改。白先生用“浓浊”这个生动形容词,让我们能透过文字来“认识”这个真实的赖鸣升:浓浊不仅说明他的口音重,更突显他声音的苍老感和浑浊有力的气魄;不仅反映出他已年纪渐长的一面,更体现出军人的铁汉血性深根在他身上。
不管岁月已在他脸上留下苍斑,皱纹如小沙丘一圈圈堆叠着,这些丝毫不影响他始终是个大气豪爽的男人。

就连被女人骗婚和卷走所有退役金的事,他也是骂过就算,还能自嘲地告诉别人,丝毫不在意会不会被取笑,有种“散尽千金还复来”的潇洒豪迈姿态。
生活的困窘压不倒他,但思乡之情却能被回忆轻易勾起。
就如他到刘营长家中与他们一家人过年,大概就是老乡情结吧。听刘营长说一口正宗的四川话,刘太太做得一手地道的四川菜,只可惜,那道“蚂蚁上树”他似乎一口也没吃。这大概是白先生故意的一笔:思乡情怯,以至于喜欢却又害怕吃到家乡味道的菜。
好比他一边喝着台湾的金门高粱,嘴上心上还对贵州的茅台念念不忘;喝得起劲时,说着他在大陆时那些或光辉或倒霉的事,就不由自主地骂咧着“龟儿子”、“妈那个巴子的”那些四川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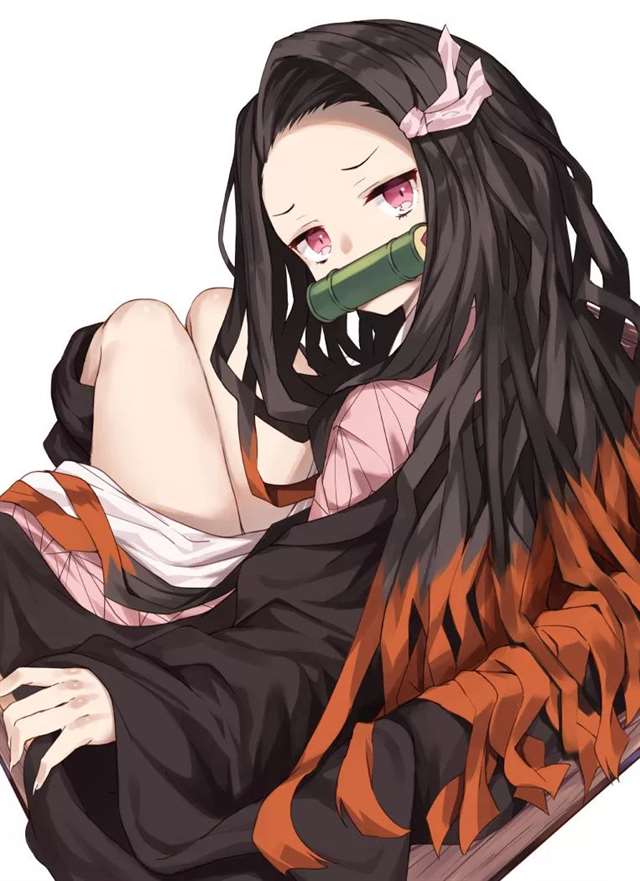
 疼才能记住我是你的男人
疼才能记住我是你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