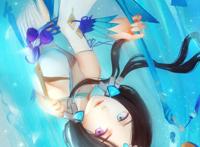被劈成两半的子爵(4)
一天晚上,奶妈房门被推开,子爵站到了她的床前。
“奶妈,您的皮肤凹凸不平与颜色深浅不一,出什么事了?”
“你的罪孽留下的痕迹,孩子。”老妇人说话时神态安详。
“您应当尽快痊愈,您的新郎还在等您,他要带您走,你不知道吗?”
“孩子,你的青春美貌被毁坏了,就不要拿上年纪的人来开心了。”
“我不是说笑话。奶妈,您听,您的未婚夫正在您的窗子下吹笛子呢。”
塞巴斯蒂安侧耳细听,听见了那个麻风病人正在城堡外面吹号角。
打那以后,我便再也没见过奶妈,我开始讨厌特里劳尼大夫。对于牲口,对于小动物,对于石头,对于一切自然现象,他满怀关注之情,可是对于人类的疾病,他心里却充满厌恶与畏惧。对于他的厌恶,我略有所知,如此作恶的子爵竟从来不生病,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我不知道他畏惧什么。
我到海边去拾螃蟹,当我在一块礁石顶上起劲地掏洞里的小螃蟹时,看见我身下平静的水面映出一把剑,锋刃正对准我的头,我惊落海里。
“抓住这里。”我舅舅说到。原来是他从背后靠拢了我,要我抓住他的剑,从剑刃那边抓。
“不,我自己来。”我回答道。我爬上一块大石头,它与礁石隔着一丈宽的水面。
“你去捉螃蟹吗?”梅达尔多说,“我逮水蛭。”他让我看他的猎物,那是一些棕白色的又粗又肥的水蛭,它们全被一劈两半,触角还在不停蠕动。
“如果能将一切东西都一劈为二的话,那么人人都可以摆脱他那愚蠢的完整概念的束缚了。我原来是完整的人,那时什么东西在我看来都是自然而混乱的,像空气一样简单。我以为什么都能看清,其实只是看到皮毛而已。假如你将变成你自己一半的话,孩子,我祝愿你如此,你便会了解用整个头脑的普通智力所不及的东西。你虽然失去了你自己和这世界的一半,但是留下的这一半将是千百倍珍贵。你也将会愿意一切东西都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变成半个,因为美好、智慧、正义只存在于被破坏之后。”
“呦,呦,”我说,“这里螃蟹真多!”我假装只对找螃蟹感兴趣,为的是远离舅舅的剑。我一直等着他带着那些水蛭走远了才回到岸上。可是他的那些话老在我耳边回响,搅得我心神不宁。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躲开他那疯狂劈砍的避难处,无论我找谁,奥多师傅,特里劳尼,塞巴斯蒂安还是麻风病人,我们大家统统都处在这个半边身子的人的威慑下,我们活在他威慑的温柔里。
“奶妈,您的皮肤凹凸不平与颜色深浅不一,出什么事了?”
“你的罪孽留下的痕迹,孩子。”老妇人说话时神态安详。
“您应当尽快痊愈,您的新郎还在等您,他要带您走,你不知道吗?”
“孩子,你的青春美貌被毁坏了,就不要拿上年纪的人来开心了。”
“我不是说笑话。奶妈,您听,您的未婚夫正在您的窗子下吹笛子呢。”
塞巴斯蒂安侧耳细听,听见了那个麻风病人正在城堡外面吹号角。
打那以后,我便再也没见过奶妈,我开始讨厌特里劳尼大夫。对于牲口,对于小动物,对于石头,对于一切自然现象,他满怀关注之情,可是对于人类的疾病,他心里却充满厌恶与畏惧。对于他的厌恶,我略有所知,如此作恶的子爵竟从来不生病,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我不知道他畏惧什么。
我到海边去拾螃蟹,当我在一块礁石顶上起劲地掏洞里的小螃蟹时,看见我身下平静的水面映出一把剑,锋刃正对准我的头,我惊落海里。
“抓住这里。”我舅舅说到。原来是他从背后靠拢了我,要我抓住他的剑,从剑刃那边抓。

“不,我自己来。”我回答道。我爬上一块大石头,它与礁石隔着一丈宽的水面。
“你去捉螃蟹吗?”梅达尔多说,“我逮水蛭。”他让我看他的猎物,那是一些棕白色的又粗又肥的水蛭,它们全被一劈两半,触角还在不停蠕动。
“如果能将一切东西都一劈为二的话,那么人人都可以摆脱他那愚蠢的完整概念的束缚了。我原来是完整的人,那时什么东西在我看来都是自然而混乱的,像空气一样简单。我以为什么都能看清,其实只是看到皮毛而已。假如你将变成你自己一半的话,孩子,我祝愿你如此,你便会了解用整个头脑的普通智力所不及的东西。你虽然失去了你自己和这世界的一半,但是留下的这一半将是千百倍珍贵。你也将会愿意一切东西都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变成半个,因为美好、智慧、正义只存在于被破坏之后。”
“呦,呦,”我说,“这里螃蟹真多!”我假装只对找螃蟹感兴趣,为的是远离舅舅的剑。我一直等着他带着那些水蛭走远了才回到岸上。可是他的那些话老在我耳边回响,搅得我心神不宁。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躲开他那疯狂劈砍的避难处,无论我找谁,奥多师傅,特里劳尼,塞巴斯蒂安还是麻风病人,我们大家统统都处在这个半边身子的人的威慑下,我们活在他威慑的温柔里。

 岳母半推半就的同意了
岳母半推半就的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