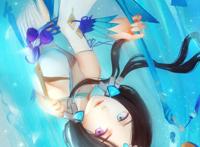被劈成两半的子爵(2)
他双臂交叉,双手抱头,踌躇满志。由残酷之战役造出流血的大地汇集了千万条血河,一直流淌到他这里;他任凭这血涛轻轻撞击自己,既无义愤填膺之感,亦无悲伤哀怜之情,仰望着波西米亚的繁星,作为子爵在大地上最后的一夜,天空不谈军衔。
他果真上了天。在马肠子露出后微笑,被土耳其人重重的轰了一炮,醒来时,他已是半身人。库尔齐奥曾提醒他,在开战前作为点将的帅,向后转,那并不吉利;但重要的是梅达尔多那另外一半身体,宣告失踪。库尔齐奥没有看清。
舅舅被人抬回泰拉尔巴时,我八岁。山谷人声鼎沸,我第一次发现围墙和塔楼快坍塌了,院子里满地泥淖,欢迎子爵回来喂猪。高大的老奶妈塞巴斯蒂安走上前去,被粗暴的黑影子整得踉跄了一下,那身躯在担架上顽强的扭动了一阵,梅达尔多就拄拐位于对面。一件戴帽子的黑斗篷从头顶垂到地面,露出半张脸。
“嘿舅舅,我也要玩捉迷藏。”我瞅准了舅舅的宽袍,他可真牛,变戏法式的藏起了他的左半身,不让我看见。
那群山羊呆呆地望着子爵,它们全被拴住了,每只羊从各自不同的位置扭过头来,很奇怪的将脑袋同脊背挤成一个直角。猪呢,反应更敏锐,它们尖叫起来,互相碰撞着肚皮要逃跑,大人们也再无法掩饰内心的惊恐,他们一哄而散,他们不是一向不喜欢玩捉迷藏的?此刻竟也这么开心?我领着几个小孩子起了哄,大人们边跑边叫我住嘴,我知道他们只是羡慕舅舅那样的本领。
舅舅从此闭门不出,塞巴斯蒂安奶妈也拿他毫无办法。他的父亲似乎早就预料到儿子回来后的阴沉与孤僻,此刻他最喜爱的,一只训练有素的小伯劳便派上了用场。
一天清晨,老人打开铁栅门,放出伯劳,看着他飞至儿子的窗口,才转身给喜鹊喂食,并学鸟儿们的啼叫。片刻之后,他听见有件东西撞到鸟笼架上,他伸头探看,只见他的伯劳僵死在檐口上。老人双手把鸟儿捧起,见它的一只翅膀折了,像是被人撕下来,一只爪子断了,似乎有人用指头硬掰的,一只眼睛也被抠去了,老人将鸟贴在胸口上,呜呜地哭了,当天就卧床不起了,仆人们从鸟笼的铁网里见他病得厉害,可是谁也无法照顾,因为他人在里面,又把钥匙藏起来了。鸟儿们都绕在他的床边飞,第二天清晨,鸟儿停栖在他的床头,好像飞落在一根海面漂浮的树干上,老人死了。
父亲死后,梅达尔多开始走出城堡,又是奶妈第一个发现的,仆人们一路小跑,来到一棵梨树下:“你们看!”他们朝着曙光逆照中挂着的梨望去,全惊呆了——梨都不是完整的了。其实也不能这么说,梨之间还是完整的,至少它们都整齐划一的保留着右半部分,被竖劈留下的右半部分。
他果真上了天。在马肠子露出后微笑,被土耳其人重重的轰了一炮,醒来时,他已是半身人。库尔齐奥曾提醒他,在开战前作为点将的帅,向后转,那并不吉利;但重要的是梅达尔多那另外一半身体,宣告失踪。库尔齐奥没有看清。
舅舅被人抬回泰拉尔巴时,我八岁。山谷人声鼎沸,我第一次发现围墙和塔楼快坍塌了,院子里满地泥淖,欢迎子爵回来喂猪。高大的老奶妈塞巴斯蒂安走上前去,被粗暴的黑影子整得踉跄了一下,那身躯在担架上顽强的扭动了一阵,梅达尔多就拄拐位于对面。一件戴帽子的黑斗篷从头顶垂到地面,露出半张脸。
“嘿舅舅,我也要玩捉迷藏。”我瞅准了舅舅的宽袍,他可真牛,变戏法式的藏起了他的左半身,不让我看见。
那群山羊呆呆地望着子爵,它们全被拴住了,每只羊从各自不同的位置扭过头来,很奇怪的将脑袋同脊背挤成一个直角。猪呢,反应更敏锐,它们尖叫起来,互相碰撞着肚皮要逃跑,大人们也再无法掩饰内心的惊恐,他们一哄而散,他们不是一向不喜欢玩捉迷藏的?此刻竟也这么开心?我领着几个小孩子起了哄,大人们边跑边叫我住嘴,我知道他们只是羡慕舅舅那样的本领。

舅舅从此闭门不出,塞巴斯蒂安奶妈也拿他毫无办法。他的父亲似乎早就预料到儿子回来后的阴沉与孤僻,此刻他最喜爱的,一只训练有素的小伯劳便派上了用场。
一天清晨,老人打开铁栅门,放出伯劳,看着他飞至儿子的窗口,才转身给喜鹊喂食,并学鸟儿们的啼叫。片刻之后,他听见有件东西撞到鸟笼架上,他伸头探看,只见他的伯劳僵死在檐口上。老人双手把鸟儿捧起,见它的一只翅膀折了,像是被人撕下来,一只爪子断了,似乎有人用指头硬掰的,一只眼睛也被抠去了,老人将鸟贴在胸口上,呜呜地哭了,当天就卧床不起了,仆人们从鸟笼的铁网里见他病得厉害,可是谁也无法照顾,因为他人在里面,又把钥匙藏起来了。鸟儿们都绕在他的床边飞,第二天清晨,鸟儿停栖在他的床头,好像飞落在一根海面漂浮的树干上,老人死了。
父亲死后,梅达尔多开始走出城堡,又是奶妈第一个发现的,仆人们一路小跑,来到一棵梨树下:“你们看!”他们朝着曙光逆照中挂着的梨望去,全惊呆了——梨都不是完整的了。其实也不能这么说,梨之间还是完整的,至少它们都整齐划一的保留着右半部分,被竖劈留下的右半部分。

 岳母半推半就的同意了
岳母半推半就的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