谵妄(3):放血(14)
她转过头,自己身旁坐着一位穿着教袍的牧首,他没有五官,脸上只有一个不断坍陷的旋涡,他一只手捧着纸筒,另一只手不住拿起筒中的肉片,往旋涡中丢,就像在吃薯片一样。
“你又打算耍什么鬼把戏?”
男人转过头来,苏报春这才注意到,他头上没有光环。
“您认错人了。虽然我们使用了他的面孔,但我想聪颖如你应当不会弄混我们,”
苏报春伸了伸手,这里没有铁砂,可不能来硬的。
“哈,别告诉我你就是那棵树,否则我可要去疯人院看看了,”
观众渐次离场,演员们却还站在台上,很快观众席上便只剩下这两个人。没有光环的萨科塔慢慢“吃”着肉片,汁液把他的指甲都染成了蓝色,与幕布几乎相同的蓝色。
“我不知道您看见了什么,视觉对我们来说仍是陌生的词汇。我们还没有用以代称的名字,或许你可以叫我们大群,因为我们数量多的缘故……”
他呼出一口气,在衣服上擦了擦手,说:
“……我们曾向造主恳求,不要让我们受苦,但无人倾听我们,他们只让我们附在猪猡身上,一个接一个溺死在海沟之中。”
“我对你,呃……你们的遭遇深表同情……”
苏报春说着站了起来,她看向观众退场的那个方向,一盏灯在那里闪烁着。
“……但我不是你的造主,我还有别的事要做,还请原……”
她起身的瞬间,宏伟的穹顶崩塌风化,水晶灯在身旁摔得粉碎,红木地板衰朽,灰石立柱坍圮,丝绒发霉灰化,台上的演员仍在,不过都化作大理石雕。时间以百年、千年为单位快放着,自然重新占领了这里,青草在脚下肆意生长,不知名的啮兽跳来跳去,花儿开了又谢,果子落了又结,双月与烈日在空中竞逐,雕塑的面容逐渐模糊,渐渐连轮廓也被磨蚀,变成单纯的石柱。在这沧海桑田之中,唯有苏报春和她身旁的男人岿然不动,仍维持着原来的样子。
她抽回自己的脚,坐回只剩铁架的椅子上。
“好吧,你赢了,你想说什么,我都洗耳恭听,”
“你又打算耍什么鬼把戏?”
男人转过头来,苏报春这才注意到,他头上没有光环。
“您认错人了。虽然我们使用了他的面孔,但我想聪颖如你应当不会弄混我们,”
苏报春伸了伸手,这里没有铁砂,可不能来硬的。
“哈,别告诉我你就是那棵树,否则我可要去疯人院看看了,”
观众渐次离场,演员们却还站在台上,很快观众席上便只剩下这两个人。没有光环的萨科塔慢慢“吃”着肉片,汁液把他的指甲都染成了蓝色,与幕布几乎相同的蓝色。
“我不知道您看见了什么,视觉对我们来说仍是陌生的词汇。我们还没有用以代称的名字,或许你可以叫我们大群,因为我们数量多的缘故……”
他呼出一口气,在衣服上擦了擦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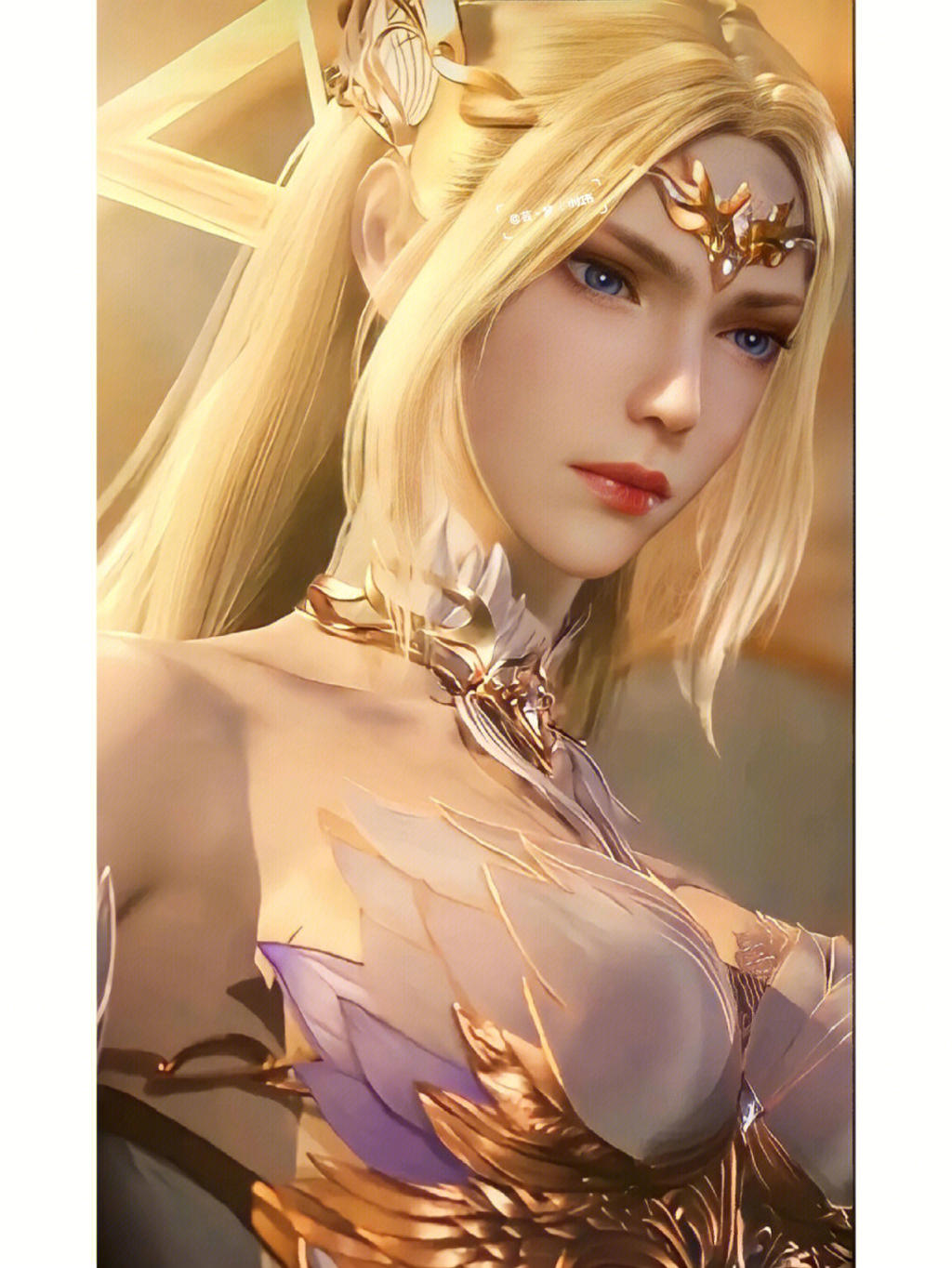
“……我们曾向造主恳求,不要让我们受苦,但无人倾听我们,他们只让我们附在猪猡身上,一个接一个溺死在海沟之中。”
“我对你,呃……你们的遭遇深表同情……”
苏报春说着站了起来,她看向观众退场的那个方向,一盏灯在那里闪烁着。
“……但我不是你的造主,我还有别的事要做,还请原……”
她起身的瞬间,宏伟的穹顶崩塌风化,水晶灯在身旁摔得粉碎,红木地板衰朽,灰石立柱坍圮,丝绒发霉灰化,台上的演员仍在,不过都化作大理石雕。时间以百年、千年为单位快放着,自然重新占领了这里,青草在脚下肆意生长,不知名的啮兽跳来跳去,花儿开了又谢,果子落了又结,双月与烈日在空中竞逐,雕塑的面容逐渐模糊,渐渐连轮廓也被磨蚀,变成单纯的石柱。在这沧海桑田之中,唯有苏报春和她身旁的男人岿然不动,仍维持着原来的样子。
她抽回自己的脚,坐回只剩铁架的椅子上。
“好吧,你赢了,你想说什么,我都洗耳恭听,”

 忍3血影x小黑
忍3血影x小黑






















![[病娇]妄想噩梦(3)](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1025/154407_034923.jpg)
![[病娇]妄想噩梦(3)](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1101/100440_18544.jpg)
![[病娇]妄想噩梦(3)](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424/162607_72372.jpg)
![[病娇]妄想噩梦(3)](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605/110419_1476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