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回来了(10)
“这该怎么解释呢?”她生气地问道,连声音都变了,“这么说,你是装的了?”
“不知道,我并不想……”
“你这孩子真难对付,”母亲说着,难过地低下头,“你走吧!!”
母亲要求我背诵的诗歌越来越多,可是我的记忆力却恶作剧似的总想把它们变变样子,改动一下,加上一些其他的词句。我要记错一首诗是轻而易举的,那些多余的词句不时地涌进我的脑海,很快就和书本上的诗句混在一起。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正行的诗在我眼前若隐若现,不管我怎样用功去记它,但总是记不住。
有一首哀伤的诗,好像是维亚捷姆斯基公爵写的,给了我极大的苦恼:
不论傍晚还是清晨,
有无数的孤寡和老人
他们呼吁救助,
凭着上帝的名分。
可是下面一行“挎着饭袋从窗下走过”,我怎么也记不住,总是把它漏掉。(维亚捷姆斯基:19世纪俄国诗人和批评家,在青年时代是普希金的朋友,但到晚年变成了保守派。)
母亲生气地把我的行为告诉了外祖父,外祖父狠狠地说:“他装蒜!他的记性好着呢,祈祷词记得比我都牢。他骗你的,他的记性像石头一样牢靠,只要刻上去,就不会忘掉!你该狠狠地揍他一顿!”
外祖母也揭发我:“故事他都记得,歌词他也记得,歌词和诗不是一回事吗?”这些话很有道理,我也觉得自己心中有愧。可是,只要我一念诗,一些不相干的词句就像成群结队的蟑螂一样,不知从哪儿爬了出来,它们也排成整齐的诗行:
“不知道,我并不想……”
“你这孩子真难对付,”母亲说着,难过地低下头,“你走吧!!”
母亲要求我背诵的诗歌越来越多,可是我的记忆力却恶作剧似的总想把它们变变样子,改动一下,加上一些其他的词句。我要记错一首诗是轻而易举的,那些多余的词句不时地涌进我的脑海,很快就和书本上的诗句混在一起。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正行的诗在我眼前若隐若现,不管我怎样用功去记它,但总是记不住。
有一首哀伤的诗,好像是维亚捷姆斯基公爵写的,给了我极大的苦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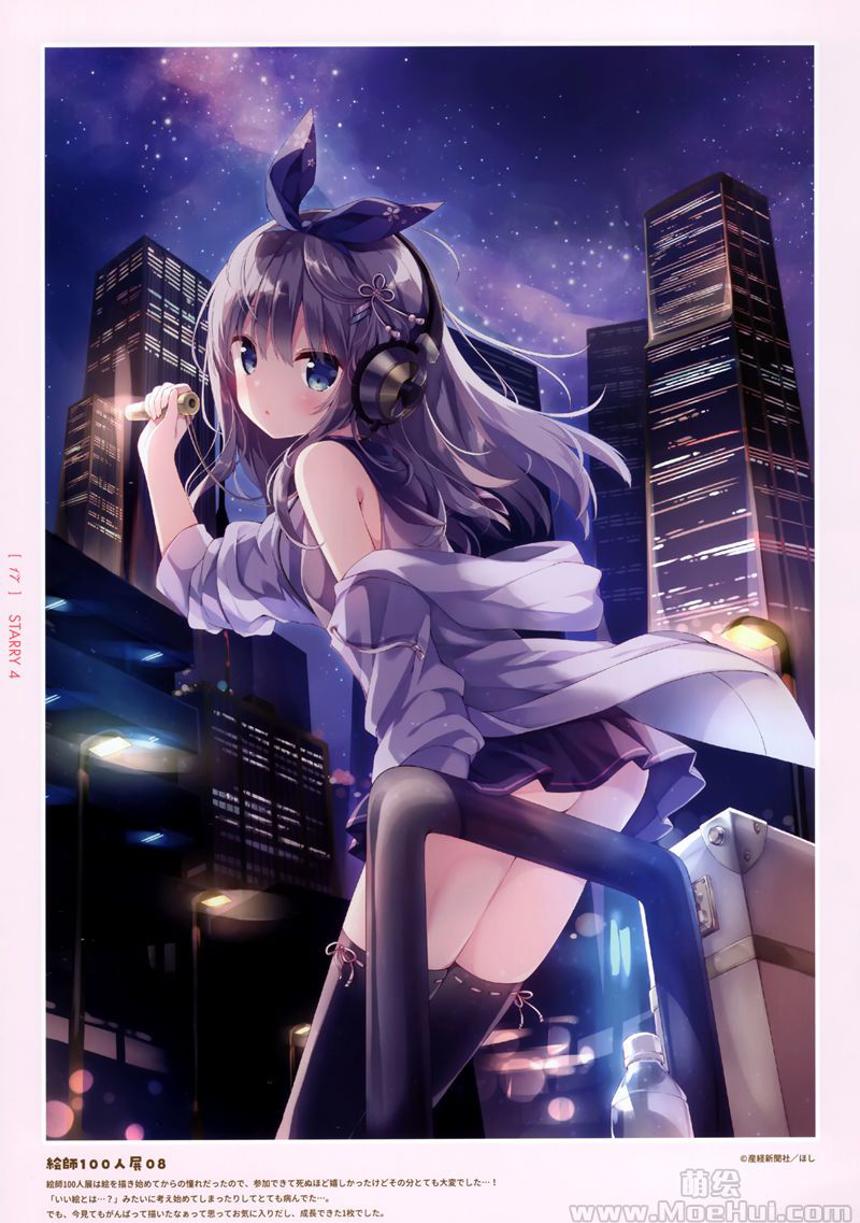
不论傍晚还是清晨,
有无数的孤寡和老人
他们呼吁救助,
凭着上帝的名分。
可是下面一行“挎着饭袋从窗下走过”,我怎么也记不住,总是把它漏掉。(维亚捷姆斯基:19世纪俄国诗人和批评家,在青年时代是普希金的朋友,但到晚年变成了保守派。)
母亲生气地把我的行为告诉了外祖父,外祖父狠狠地说:“他装蒜!他的记性好着呢,祈祷词记得比我都牢。他骗你的,他的记性像石头一样牢靠,只要刻上去,就不会忘掉!你该狠狠地揍他一顿!”
外祖母也揭发我:“故事他都记得,歌词他也记得,歌词和诗不是一回事吗?”这些话很有道理,我也觉得自己心中有愧。可是,只要我一念诗,一些不相干的词句就像成群结队的蟑螂一样,不知从哪儿爬了出来,它们也排成整齐的诗行:

 龙母怀孕大肚子要生了
龙母怀孕大肚子要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