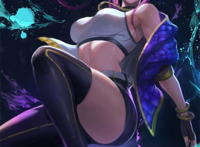王文泸:马经(5)
前文写到都兰的那15匹殉葬马,我发现脑门上都有一个略小于拳头的洞,边缘参差不齐。我曾猜想,这个洞一定是致马于死地的伤口。不可能把马提前杀死,再把尸体抬进去殉葬。是用活马殉葬。活马在墓坑里受惊乱跳,怎么弄死它?我猜想,先在墓穴里设置一副结实的木头架子,把马牵进去绑好,殉马师举起铁锤,往马的颅骨正中(那是最脆弱的部位)大力一击,骏马立即倒地。后来一想不对,人家根本用不着什么木头架子,只要用一块布把马的眼睛蒙上,就不必担心马匹躲闪。
肯定是这样,要不然脑门上哪来这个洞呢?
想想人类的这些残忍,就觉得,生前安享尊荣的墓主人死后被人掘墓,暴尸天日之下,真是活该。
跟人一样,马匹禀赋不同,脾气各异。你和它们相逢于偶然,结缘于他乡,周旋于晨夕。它们或与你对抗,或让你畏惧,或与你默契,或让你敬佩。虽属异类,也会撩动起你与人相处时常有的情感。
有几匹马让我终生难忘。
在甘青交界处发生草山纠纷时,我领命带队前往支援。我的坐骑大枣骝,是一匹惯于跋山涉水的老江湖。它强健、机敏、忠诚,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在危境中有了依赖。途经涨了水的老虎沟,面对滔滔浊浪,马匹们都本能地躲闪着,死活不肯下水,队员说:“咋办呀王同志?得有一匹马领个头!现在只有指望大枣骝了。你胆子放大。趁早把脚从镫里脱开,万一被河水冲翻了,牢牢抓住马镫或是马尾巴!”
在我再三催促之下,大枣骝低头嗅闻着河水,“噗噗”地打着响鼻,终于下了水。它高昂着头颅,谨慎地抬腿、落蹄,探索着浊浪底下的乱石,稳步前行,像老练的水手。浪头打湿了马鞍,淹过了我蜷曲的双脚,我知道自己的脸色已经发白,但大枣骝没有慌乱。身后疑惧不安的响鼻告诉我,别的马匹跟上来了。
这一年大枣骝已经十三岁,老了,是个老英雄。
大枣骝后来伤了腿,我换乘一匹外号叫“黄沙燕”的“战备马”。这是一匹脾气暴躁、有强烈争先意识的家伙。马队出行,它总要走在最前边。不时抿起耳朵,撕咬试图超过它的同类。稍一放松辔绳,就想撒开四蹄。骑行一天,勒马勒得人手臂酸疼。有一次,一行七八骑,从陡坡登上了一处宽阔无垠的草甸,有人想开个玩笑,突然怪叫一声,黄沙燕误以为听到了冲锋的口令,狂烈地爆发出一直被约束着的力量,瞬间和马队拉开了距离。而远处的地平线上,一群藏狗闻声飞奔而来。我双手紧勒辔绳,身体直往后仰,很奇怪竟然勒不疼它。原来这个狡猾的家伙已经用牙齿咬住了嚼铁。眨眼之间,五六只壮如牛犊的藏狗呈扇面吼奔而至,“嘭”的一声,辔绳被我拽断,草地迎面扑来,我感到身体砸向地面时可怕的重量。与此同时,黄沙燕突然“刹车”,“咴咴”嘶叫着,抬起惯于打人的前蹄。
肯定是这样,要不然脑门上哪来这个洞呢?
想想人类的这些残忍,就觉得,生前安享尊荣的墓主人死后被人掘墓,暴尸天日之下,真是活该。
跟人一样,马匹禀赋不同,脾气各异。你和它们相逢于偶然,结缘于他乡,周旋于晨夕。它们或与你对抗,或让你畏惧,或与你默契,或让你敬佩。虽属异类,也会撩动起你与人相处时常有的情感。
有几匹马让我终生难忘。
在甘青交界处发生草山纠纷时,我领命带队前往支援。我的坐骑大枣骝,是一匹惯于跋山涉水的老江湖。它强健、机敏、忠诚,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在危境中有了依赖。途经涨了水的老虎沟,面对滔滔浊浪,马匹们都本能地躲闪着,死活不肯下水,队员说:“咋办呀王同志?得有一匹马领个头!现在只有指望大枣骝了。你胆子放大。趁早把脚从镫里脱开,万一被河水冲翻了,牢牢抓住马镫或是马尾巴!”

在我再三催促之下,大枣骝低头嗅闻着河水,“噗噗”地打着响鼻,终于下了水。它高昂着头颅,谨慎地抬腿、落蹄,探索着浊浪底下的乱石,稳步前行,像老练的水手。浪头打湿了马鞍,淹过了我蜷曲的双脚,我知道自己的脸色已经发白,但大枣骝没有慌乱。身后疑惧不安的响鼻告诉我,别的马匹跟上来了。
这一年大枣骝已经十三岁,老了,是个老英雄。
大枣骝后来伤了腿,我换乘一匹外号叫“黄沙燕”的“战备马”。这是一匹脾气暴躁、有强烈争先意识的家伙。马队出行,它总要走在最前边。不时抿起耳朵,撕咬试图超过它的同类。稍一放松辔绳,就想撒开四蹄。骑行一天,勒马勒得人手臂酸疼。有一次,一行七八骑,从陡坡登上了一处宽阔无垠的草甸,有人想开个玩笑,突然怪叫一声,黄沙燕误以为听到了冲锋的口令,狂烈地爆发出一直被约束着的力量,瞬间和马队拉开了距离。而远处的地平线上,一群藏狗闻声飞奔而来。我双手紧勒辔绳,身体直往后仰,很奇怪竟然勒不疼它。原来这个狡猾的家伙已经用牙齿咬住了嚼铁。眨眼之间,五六只壮如牛犊的藏狗呈扇面吼奔而至,“嘭”的一声,辔绳被我拽断,草地迎面扑来,我感到身体砸向地面时可怕的重量。与此同时,黄沙燕突然“刹车”,“咴咴”嘶叫着,抬起惯于打人的前蹄。

 王者荣耀马超囚禁司马懿
王者荣耀马超囚禁司马懿





















![[僵约]重生马小玲之改变宿命 38 人王与瑶池圣母的曾经爱情故事 下](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517/180525_57823.jpg)
![[僵约]重生马小玲之改变宿命 38 人王与瑶池圣母的曾经爱情故事 下](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601/171256_092016.jpg)
![[僵约]重生马小玲之改变宿命 38 人王与瑶池圣母的曾经爱情故事 下](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1025/154403_57048.jpg)
![[僵约]重生马小玲之改变宿命 38 人王与瑶池圣母的曾经爱情故事 下](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306/153219_18838.jpg)
![[僵约]重生马小玲之改变宿命 37 人王与瑶池圣母曾经的爱情故事 上](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428/161505_95564.jpg)
![[僵约]重生马小玲之改变宿命 37 人王与瑶池圣母曾经的爱情故事 上](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1101/105139_58813.jpg)
![[僵约]重生马小玲之改变宿命 37 人王与瑶池圣母曾经的爱情故事 上](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403/171950_086119.jpg)
![[僵约]重生马小玲之改变宿命 37 人王与瑶池圣母曾经的爱情故事 上](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412/173952_9797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