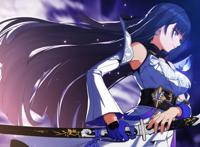一事无成(2)
快点快点。
就好像这个声音的意志先一步控制程末的身体,领先于他的焦急,它比焦急还快,程末的内心还正如旭阳般烈火焦急,它就已经占据了神经元向身体发出指令,又正如他的迷茫,他的迷茫和焦急正像他上学期挂科灼灼其华的成绩单信息被他爸妈悉知的时候,这个声音的意志又控制他的双手和头脑出现在了召唤师峡谷,控制他选择了盲僧,控制他就算o干4天崩开局,嘴角也呢喃着盲僧的台词,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
正当程末的焦急还在蓄力阶段连释放都尚未表露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体带着如同热泪盈眶般的汗水蒸发的大量的H2O--水和少量的NaCl --氯化钠(盐),哦,对了,还有微乎其微的占百分之一二的少量尿素、乳酸和脂肪酸,就进入了教室。带着油腻眼镜的秃顶着几根吊毛的数学老师头也不抬拿着花名册问道程末叫叫什么名字。程末脸色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不落帝国一样迟暮般跨了下去,心像幽邃的海底褪去了所有的焦急沉默了阳光般沉下去,他缓缓得慢吞到像挂上了沉重的各种主义的枷锁般念出自己的名字,程末,音节的跳动像个难产而死的胚胎。
数学老师依旧没有抬头,就像一尊沉思者高贵的头颅,他只是再花名册上打上应该扣的学分。笔迹干净整洁,力道整齐划一,就好像是正统的理科男做着无关任何人任何事只是天性严谨的塑造着另人沉醉的艺术品。他只是推了一下他的无框眼镜,就好像欣赏和校正一下他创造的数学符号到令他满意的程度。以至于他从未抬起头看沉默一眼,他接着看起了备课本,似乎措辞和斟酌这节高数的开场白和今天该抽哪一个学号的幸运儿来回答他现在精心设计的上节课内容的问题。他低下头时头上的荒原有多么得胸怀宽广、袒胸露乳,他就有多么地不在乎程末。
尽管程末知道这不是一种轻蔑,他知道数学老师名字,知道他的为人师表正如其名--
高严,程末更愿意称之为这是一种与生俱来而浑然天成的习惯。程末理解老高,但并不妨碍他像大部分学生在私下窃窃私语高严为狗头老高一样在心里一遍又一遍痛斥着狗头老高,这种无能为力的恼怒在沉默悻悻得在最后一排随意坐下时看见猪头张偷偷摸摸从教室后门溜进来坐在他身旁,而狗头老高却依旧头也不抬构思他美妙的构想时,这种择人而噬的恼怒犹如行军蚁般野火燃烧般剧烈卷席开来而去啃噬程末的内心,他体内的理智如同他刚刚挥发的汗水一样,近乎哀嚎般地撕裂蒸发在空气之中,而这种空气变成了令他自己都感到窒息的氛围。
这不公平,尽管这看起来像一件日常生活中无足挂齿小事般的不公平,可程末的心里内只有在想,为什么只有他被扣学分,被大庭广众之下被众目睽睽地无视,近乎被宣判形式地剥夺尊严,就好像藏在阴暗角落里的蚯蚓,被人一锄头下去连泥带土地体无完肤地暴露在诸多令他感到不适的带有各式各样别有目的的想法的目光之中,蚯蚓会不开心得如同丧家之犬般奔逃着钻入它熟悉的温暖潮湿又黑暗的土壤之中,何况是沉默。凭什么,凭什么,他的室友在一样的土壤之下却可以堂而皇之地不被人翻出忍受所有人凛冽的目光和冰冷的锄头的侮辱,凭什么!只因为他是一只幸运的蚯蚓,可以安详地在他微乎其微距离的土壤里傲游着,藏匿着。
就好像这个声音的意志先一步控制程末的身体,领先于他的焦急,它比焦急还快,程末的内心还正如旭阳般烈火焦急,它就已经占据了神经元向身体发出指令,又正如他的迷茫,他的迷茫和焦急正像他上学期挂科灼灼其华的成绩单信息被他爸妈悉知的时候,这个声音的意志又控制他的双手和头脑出现在了召唤师峡谷,控制他选择了盲僧,控制他就算o干4天崩开局,嘴角也呢喃着盲僧的台词,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
正当程末的焦急还在蓄力阶段连释放都尚未表露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体带着如同热泪盈眶般的汗水蒸发的大量的H2O--水和少量的NaCl --氯化钠(盐),哦,对了,还有微乎其微的占百分之一二的少量尿素、乳酸和脂肪酸,就进入了教室。带着油腻眼镜的秃顶着几根吊毛的数学老师头也不抬拿着花名册问道程末叫叫什么名字。程末脸色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不落帝国一样迟暮般跨了下去,心像幽邃的海底褪去了所有的焦急沉默了阳光般沉下去,他缓缓得慢吞到像挂上了沉重的各种主义的枷锁般念出自己的名字,程末,音节的跳动像个难产而死的胚胎。
数学老师依旧没有抬头,就像一尊沉思者高贵的头颅,他只是再花名册上打上应该扣的学分。笔迹干净整洁,力道整齐划一,就好像是正统的理科男做着无关任何人任何事只是天性严谨的塑造着另人沉醉的艺术品。他只是推了一下他的无框眼镜,就好像欣赏和校正一下他创造的数学符号到令他满意的程度。以至于他从未抬起头看沉默一眼,他接着看起了备课本,似乎措辞和斟酌这节高数的开场白和今天该抽哪一个学号的幸运儿来回答他现在精心设计的上节课内容的问题。他低下头时头上的荒原有多么得胸怀宽广、袒胸露乳,他就有多么地不在乎程末。

尽管程末知道这不是一种轻蔑,他知道数学老师名字,知道他的为人师表正如其名--
高严,程末更愿意称之为这是一种与生俱来而浑然天成的习惯。程末理解老高,但并不妨碍他像大部分学生在私下窃窃私语高严为狗头老高一样在心里一遍又一遍痛斥着狗头老高,这种无能为力的恼怒在沉默悻悻得在最后一排随意坐下时看见猪头张偷偷摸摸从教室后门溜进来坐在他身旁,而狗头老高却依旧头也不抬构思他美妙的构想时,这种择人而噬的恼怒犹如行军蚁般野火燃烧般剧烈卷席开来而去啃噬程末的内心,他体内的理智如同他刚刚挥发的汗水一样,近乎哀嚎般地撕裂蒸发在空气之中,而这种空气变成了令他自己都感到窒息的氛围。
这不公平,尽管这看起来像一件日常生活中无足挂齿小事般的不公平,可程末的心里内只有在想,为什么只有他被扣学分,被大庭广众之下被众目睽睽地无视,近乎被宣判形式地剥夺尊严,就好像藏在阴暗角落里的蚯蚓,被人一锄头下去连泥带土地体无完肤地暴露在诸多令他感到不适的带有各式各样别有目的的想法的目光之中,蚯蚓会不开心得如同丧家之犬般奔逃着钻入它熟悉的温暖潮湿又黑暗的土壤之中,何况是沉默。凭什么,凭什么,他的室友在一样的土壤之下却可以堂而皇之地不被人翻出忍受所有人凛冽的目光和冰冷的锄头的侮辱,凭什么!只因为他是一只幸运的蚯蚓,可以安详地在他微乎其微距离的土壤里傲游着,藏匿着。
 无一郎和有一郎搞笑日常
无一郎和有一郎搞笑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