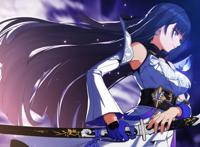一事无成(8)
程末凝视完,内心对寒冷的自我的悲哀更深了一层。他也没有表现出来,猪头张兴冲冲捅着他的胳肢窝叫他去大食堂干饭,他也戴好快乐的面具,像往常一样和猪头张谈天说地地结伴而行奔赴向人生的平庸的宴会。程末的心怀不满和愤世嫉俗早已烟消云散,他的内心无比平静,平静像条食堂阿姨每天在泔水处心心善善喂养的一条流浪的瘦瘦的中华田园犬,平静得他可以戴好他的面具,也可以做他现在觉得需要做的事。他没有去追赶向老高道歉,他也一并戴着面具和猪头张继续嘻嘻哈哈活得无忧无虑没心没肺。他明白问题没有出在这些之中,无论道歉与否,戴不戴面具做这些事,他仰望老高,他也默认接受猪头张心存好意的与他一起干一些无聊却能快速度过懒洋洋的时间的事情,他明白问题出在自己,他并没有找到自己令自己不再惶恐不安隐秘的渴望,他很平庸,一事无成得时令自己内心煎熬且自我麻痹变成进退维谷的反复的自我拷问。
但程末上了老高的这节数学课,他最大的收获并不是拉格朗日的故事,也不是他分析了自己的平庸与一事无成,而是获得了自己的心如止水,程末知道他自己的内心和身体的不平衡,但他也已不再拘泥于自己的内心,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学分,自己戴上的面具,自己陪伴的猪头张,说到猪头张,他现在总是嘴角挂起莫名笑意得想起罗翔老师说过的话-他李四的事,关我张三什么事-好像确实一直不关猪头张的事,都是程末自己的事,想到这,程末不禁哑然失笑。噢,对了,还有不是自己的老高-他浩瀚如星辰。
入学的第一个星期,程末不明白为什么学长们喜欢跑到广阔的天台扶着天台栏杆有着倦怠和写意地不惊不扰地看向远方的错落的迷蒙的群山抽着廉价的二手烟。可是,好像总是要经历过某些时间忧心忡忡的洗练,程末才能明白学长们的些许抽烟的感受,说什么唏嘘的感同身受,莫不如像洗衣机的滚筒一样经历一圈时间的轮回。重新来过。
程末和猪头张扒拉完大米饭。
独自上了天台,在栏杆处被凛冽的风吹着,被远处无声静默地呐喊着,仿若鲁迅门前三棵枣树生来就被询问由来的仿徨。他也没有带上小卖部贩卖的大前门,想必心里的空落还差些火候,只是他眸子星光暗暗淡看着远方,也没有了从百草园杀到三味书屋的勇气,他只是望向远处高楼大厦旁霓虹灯下蝼蚁般的车水马龙,就像望向了以后在拥挤的车流中手握皮革味刺鼻的五菱神车方向盘并抽着吊烟把烟灰百无聊赖地弹出半开玻璃着的车窗外然后沉默地听着汽车广播里千疮百孔的爱情故事和等待着红绿灯的自己。他回想起自己在恍惚逝去的青春中做过类似几个相同的梦境,梦境之中总有几个先哲碎碎嘴更像个更年期的老太婆穿着90年代流行的碎花裙子念叨着箴言:
人活着最随处可见的是盛大的平庸,而人生着就是在平庸中寻找前进的方向。
至此,程末拍了拍身上形如枯槁的尘埃落定。
但程末上了老高的这节数学课,他最大的收获并不是拉格朗日的故事,也不是他分析了自己的平庸与一事无成,而是获得了自己的心如止水,程末知道他自己的内心和身体的不平衡,但他也已不再拘泥于自己的内心,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学分,自己戴上的面具,自己陪伴的猪头张,说到猪头张,他现在总是嘴角挂起莫名笑意得想起罗翔老师说过的话-他李四的事,关我张三什么事-好像确实一直不关猪头张的事,都是程末自己的事,想到这,程末不禁哑然失笑。噢,对了,还有不是自己的老高-他浩瀚如星辰。

入学的第一个星期,程末不明白为什么学长们喜欢跑到广阔的天台扶着天台栏杆有着倦怠和写意地不惊不扰地看向远方的错落的迷蒙的群山抽着廉价的二手烟。可是,好像总是要经历过某些时间忧心忡忡的洗练,程末才能明白学长们的些许抽烟的感受,说什么唏嘘的感同身受,莫不如像洗衣机的滚筒一样经历一圈时间的轮回。重新来过。
程末和猪头张扒拉完大米饭。
独自上了天台,在栏杆处被凛冽的风吹着,被远处无声静默地呐喊着,仿若鲁迅门前三棵枣树生来就被询问由来的仿徨。他也没有带上小卖部贩卖的大前门,想必心里的空落还差些火候,只是他眸子星光暗暗淡看着远方,也没有了从百草园杀到三味书屋的勇气,他只是望向远处高楼大厦旁霓虹灯下蝼蚁般的车水马龙,就像望向了以后在拥挤的车流中手握皮革味刺鼻的五菱神车方向盘并抽着吊烟把烟灰百无聊赖地弹出半开玻璃着的车窗外然后沉默地听着汽车广播里千疮百孔的爱情故事和等待着红绿灯的自己。他回想起自己在恍惚逝去的青春中做过类似几个相同的梦境,梦境之中总有几个先哲碎碎嘴更像个更年期的老太婆穿着90年代流行的碎花裙子念叨着箴言:
人活着最随处可见的是盛大的平庸,而人生着就是在平庸中寻找前进的方向。

至此,程末拍了拍身上形如枯槁的尘埃落定。
 无一郎和有一郎搞笑日常
无一郎和有一郎搞笑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