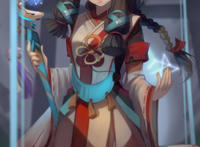锡安无战事 · 第一幕(8)
老兵咧着嘴,烈酒几乎烧的他的胡子都翘起来了。“咱们的代表在苏黎世区签了和平协定,明天开始,数三个月,我们就能回家了。”
我先是愣怔,再是惊讶,最后我才发现我应该在逐渐被喜悦淹没:“真的呀?我们都能回家了?”我双手握拳,重复着这句话。三个月不算什么,为了这个停战,我已经度过了七百多个在战壕、在废墟、在街垒里风吹日晒雨淋,还要时刻提防花旗佬摸过来的日子。三个月!这场该死的战争就结束了,我可以回家,也可以去做一阵子工赚够钱再回去。我要带上一肚子故事,披挂好的礼品和军装,去敲开家门,然后也像卡岑斯基和他的母亲一样与我的母亲抱在一起。那些礼品还有一些要给邻居的,他们帮了我家很多的忙……
“你看起来真是闪闪发光,小子。”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可是,老伊,你怎么不那么高兴?”
伊格纳特沉吟片刻,好像在思索要不要说出来一样。最后他还是说了:“马上,我们要来补充兵员了,我听连里的文书说,没几天就要开拔。”他灌了一口酒,望向身后激动的人群,乔立、彼得、帕夫列维奇、索尔他们也在其中。“这次我们要去的是伊索尔达区的突出部。在那里守到停战。”
过了半个世纪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伊索尔达,绞肉机,那片我们和花旗佬打了两次的地方?”
伊格纳特点点头。“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孩子……但是战争还没结束。不过,多少有点指望了,不是吗?”
我没回答,而是垂下头来。两年间,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想肆无忌惮地哭一场,既为了这该死的战争,该死的光荣和梦想,该死的三个月,该死的联合政府、指挥部和企业,他们阴搓搓地替我们开战,又不情愿地替我们宣布停火。只要三个月,九十天,2160个小时,然后大家就可以放下枪回到家过日子。但是在这之前,我和或拐来或强征来或自愿来的同袍们还得挤在一个战壕里,往对面的花旗佬脸上倾泻子弹和血。战争毕竟没有结束,而双方还都有趁着全面停火前或扩大,或维护己方利益的意思,后方的指挥部一声令下,他们知道无论如何星条旗都打不到他们那里,而却要这场死亡乐透势不可避地在前线进行下去。这一点也不公平。
杯里的葡萄酒在明暗不定的灯光下显出浑浊的红色。我抓起它,然后一饮而尽。
我才十六岁,而且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活到十七岁,但我决定做点什么。
“安德烈,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来了?”卡岑斯基半睁着眼皮,我坐在他的床边。这时他已经发烧一阵子了,刚刚才醒过来。我们的周围乱糟糟的,这是因为一列向后方转运的伤兵火车到达,医生们正在挑选伤员,当然是有救治价值的那些。医生几次在我们这个房间门口走过,但从未走进来。
我先是愣怔,再是惊讶,最后我才发现我应该在逐渐被喜悦淹没:“真的呀?我们都能回家了?”我双手握拳,重复着这句话。三个月不算什么,为了这个停战,我已经度过了七百多个在战壕、在废墟、在街垒里风吹日晒雨淋,还要时刻提防花旗佬摸过来的日子。三个月!这场该死的战争就结束了,我可以回家,也可以去做一阵子工赚够钱再回去。我要带上一肚子故事,披挂好的礼品和军装,去敲开家门,然后也像卡岑斯基和他的母亲一样与我的母亲抱在一起。那些礼品还有一些要给邻居的,他们帮了我家很多的忙……
“你看起来真是闪闪发光,小子。”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可是,老伊,你怎么不那么高兴?”
伊格纳特沉吟片刻,好像在思索要不要说出来一样。最后他还是说了:“马上,我们要来补充兵员了,我听连里的文书说,没几天就要开拔。”他灌了一口酒,望向身后激动的人群,乔立、彼得、帕夫列维奇、索尔他们也在其中。“这次我们要去的是伊索尔达区的突出部。在那里守到停战。”
过了半个世纪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伊索尔达,绞肉机,那片我们和花旗佬打了两次的地方?”

伊格纳特点点头。“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孩子……但是战争还没结束。不过,多少有点指望了,不是吗?”
我没回答,而是垂下头来。两年间,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想肆无忌惮地哭一场,既为了这该死的战争,该死的光荣和梦想,该死的三个月,该死的联合政府、指挥部和企业,他们阴搓搓地替我们开战,又不情愿地替我们宣布停火。只要三个月,九十天,2160个小时,然后大家就可以放下枪回到家过日子。但是在这之前,我和或拐来或强征来或自愿来的同袍们还得挤在一个战壕里,往对面的花旗佬脸上倾泻子弹和血。战争毕竟没有结束,而双方还都有趁着全面停火前或扩大,或维护己方利益的意思,后方的指挥部一声令下,他们知道无论如何星条旗都打不到他们那里,而却要这场死亡乐透势不可避地在前线进行下去。这一点也不公平。
杯里的葡萄酒在明暗不定的灯光下显出浑浊的红色。我抓起它,然后一饮而尽。
我才十六岁,而且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活到十七岁,但我决定做点什么。
“安德烈,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来了?”卡岑斯基半睁着眼皮,我坐在他的床边。这时他已经发烧一阵子了,刚刚才醒过来。我们的周围乱糟糟的,这是因为一列向后方转运的伤兵火车到达,医生们正在挑选伤员,当然是有救治价值的那些。医生几次在我们这个房间门口走过,但从未走进来。

 王一博做肖战第一次做
王一博做肖战第一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