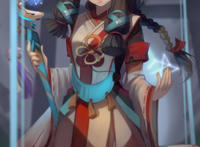锡安无战事 · 第一幕(7)
我转身离开,穿过一层层门后传出的呼喊呻吟。在医院门口,我赶上了正等着我的同伴们。已经是日暮西山的时候,夜间的冷风初起,他们在讨论着什么。我无心去听,只是在回去的路上想着,去哪里弄到这么大一笔钱。事到如今,向同伴们借不可避免地要解释,而且大家都是穷光蛋。
我动了一个念头,并且很快为之感到羞愧:卡岑斯基的包里,有一只品相很不错的瑞士表。那是他的母亲,一位胖胖的裹着花布头巾的妇人在车站为他戴上的,他父亲的手表。那天他被他的母亲紧紧地抱了很长时间,久到车要开了才依依不舍地放开。“照顾好你自己!”胖胖的妇人大声嘱咐道,“别忘了给你的表上发条!”卡岑斯基大窘,之后的日子里我们也没少拿这件逸闻涮他。
但再窘迫的时候,我们也没动过彼此的财物的主意。我听说过有那种乌鸦一样的小老百姓,在打完仗后去席卷尸体身上的财物。这些小老百姓有些披上军装,但本性难移。我还知道救助站、医院的护工是如何处置那些无人认领,死在医院里的伤兵的随身物品的,对以上两种人,我和伙伴们都嗤之以鼻。
但为什么,为什么我刚刚有那么一丁点把这手表据为己有的念头呢?“他很可能将要不久于人世了,你心知肚明。但只要在你现在拥有的钱里加上那么一块表,你就可以让你的母亲,你的温厚的母亲不留下后遗症……”思绪穿插着我,缠扰着我,我身子一阵一阵地发冷,很想喝点烈酒。
帕夫列维奇拍拍我的肩膀,“虽然你们是最好的朋友,但你还是别太难过了,安德烈。话说我对你说得那个假肢还挺感兴趣的,真的能——”
“别想了。”索尔扯了几根草放进嘴里叼着。
“你认为?”
“够呛。”索尔说。
我们沉默地在寒风中走啊,走啊,直到瘦小的乔立突然把香烟狠狠地扔到地上,他跺着脚,面目扭曲,申请狰狞。他的眼睛已经红了,像一条恶犬一样看着周围逐渐暗淡下来的天气:
“操他的,天杀的,该死,该死,该死!”
我们沉默地向前,走了很久,乔立才逐渐平静下来。每个人都知道,在前线待久了的士兵,总会有这样的崩溃时刻,只是每个人的表现不同。该给我们配备一些心理医生的,可是我们没有;甚至神职人员也行,但我们也没有神父可以告解。
今晚的晚餐很丰盛,还有晚餐酒可以享用。我和伙伴们大吃特吃,连里一多半的人都来用餐了。久别科夫也坐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吃喝谈天。“我的伙计们,我的兄弟们!”酒酣饭畅,厨师长站起来高声说道:“这顿是敬你们的,酒是我请的,你们为了所有人流血牺牲,你们值得这一切!”他圆润的胳臂抬起,“敬我们共同的光荣和梦想!”
大家都敲着桌子,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我偷偷问一直呆在营地里的伊格纳特:“这是怎么啦?”
我动了一个念头,并且很快为之感到羞愧:卡岑斯基的包里,有一只品相很不错的瑞士表。那是他的母亲,一位胖胖的裹着花布头巾的妇人在车站为他戴上的,他父亲的手表。那天他被他的母亲紧紧地抱了很长时间,久到车要开了才依依不舍地放开。“照顾好你自己!”胖胖的妇人大声嘱咐道,“别忘了给你的表上发条!”卡岑斯基大窘,之后的日子里我们也没少拿这件逸闻涮他。
但再窘迫的时候,我们也没动过彼此的财物的主意。我听说过有那种乌鸦一样的小老百姓,在打完仗后去席卷尸体身上的财物。这些小老百姓有些披上军装,但本性难移。我还知道救助站、医院的护工是如何处置那些无人认领,死在医院里的伤兵的随身物品的,对以上两种人,我和伙伴们都嗤之以鼻。
但为什么,为什么我刚刚有那么一丁点把这手表据为己有的念头呢?“他很可能将要不久于人世了,你心知肚明。但只要在你现在拥有的钱里加上那么一块表,你就可以让你的母亲,你的温厚的母亲不留下后遗症……”思绪穿插着我,缠扰着我,我身子一阵一阵地发冷,很想喝点烈酒。
帕夫列维奇拍拍我的肩膀,“虽然你们是最好的朋友,但你还是别太难过了,安德烈。话说我对你说得那个假肢还挺感兴趣的,真的能——”
“别想了。”索尔扯了几根草放进嘴里叼着。
“你认为?”
“够呛。”索尔说。
我们沉默地在寒风中走啊,走啊,直到瘦小的乔立突然把香烟狠狠地扔到地上,他跺着脚,面目扭曲,申请狰狞。他的眼睛已经红了,像一条恶犬一样看着周围逐渐暗淡下来的天气:
“操他的,天杀的,该死,该死,该死!”
我们沉默地向前,走了很久,乔立才逐渐平静下来。每个人都知道,在前线待久了的士兵,总会有这样的崩溃时刻,只是每个人的表现不同。该给我们配备一些心理医生的,可是我们没有;甚至神职人员也行,但我们也没有神父可以告解。
今晚的晚餐很丰盛,还有晚餐酒可以享用。我和伙伴们大吃特吃,连里一多半的人都来用餐了。久别科夫也坐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吃喝谈天。“我的伙计们,我的兄弟们!”酒酣饭畅,厨师长站起来高声说道:“这顿是敬你们的,酒是我请的,你们为了所有人流血牺牲,你们值得这一切!”他圆润的胳臂抬起,“敬我们共同的光荣和梦想!”
大家都敲着桌子,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我偷偷问一直呆在营地里的伊格纳特:“这是怎么啦?”

 王一博做肖战第一次做
王一博做肖战第一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