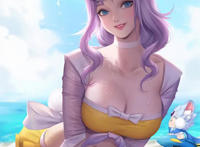【克吧征文】铁屋(4)
如今,我可以肯定,我十二分的肯定,我仍旧忌惮那魔怔的天外之音。我鼓起勇气拉起窗帘,惊悸往往只要一眼就足够了,蜷缩在这方铁皮屋中,张开嘴,却发不出一丝喘息。那斑暗锈不叫厄里倪厄斯,而是名唤格赫罗斯。
这里也是待不下去了……人类不在爆发中破灭,于是在陨落中消散。好几天我都闭关自守,靠灌安眠药度日。在二层的最后一天无事发生,某位女仆找来要我开镇定剂,说是仅剩的用完了。“谢谢,明年还您。”她走时没头没脑冒了句。
请容我将三楼的样子描摹一下,它显得极不规整,中间空出厅堂,黑绒帷幔挂满壁,天花板中央香烛正哔啵燃烧。房间在四周绕成“口”状集合式公寓那种套间。
倘若不是病人,我会喜欢这里的。身为厌食症患者又偏偏穿红挂绿,突兀的肋排和盆骨令我无端联想到蚂蚁的身材,他们要是膝行,形态也近乎如此吧。更怪异莫过于他们全无抑郁,只是卧床并极不情愿地被输液活下去。连开药都省了的我曾有意无意、试探着询问他们厌食的缘由,只换来一些审题失误:“这是奉献。”——总结,他们的灵魂始终游离在另一个世界。以及不知为何,他们某日会从床上爬起开始为期多天的填鸭式暴食,往后又重返舞台一动不动,如此反复挣扎多次才死去,莫非自虐真有什么快感?
31日早,我第一次在工作时遇见男性员工。我注意到他指尖惨白干瘪,骨节红肿,皲破、裂口都用绷带裹起,饥饿、劳碌分明在他脸边推出两片颧骨。“借一步说话。”他从脖子上摘下备用钥匙打开后门,于是老屋和我的心上都豁然开出个口子——不远处,江两侧的灯影在水中漾开,夏风挟着城市的呼吸掠过耳廓,雨后空气自带一股腐殖土的气息——那时我突然发觉自己宅居太久了。后院种满花草,虞美人的浓重快要揉碎我的眼球。四楼的哥特式窗框又高又窄,一道灰纱掩盖住内景。到天台后,他开始晾晒衣物,床单扑满晨风,飞扬……末了,他背倚铁栏杆向我兜售有神论。“喂,什么时候跟他们学上的?”我不留情面地打断他,“所以你绝食图个什么,等着再过几天一起去挺尸?”“不,医生,您误会了,实在不行算作慢性自杀好了——毕竟这的确难以理解。唔,你在乎过月球和火星上的人什么样子了么?
还有那死星,人流照旧熙熙攘攘,砸掉了闹钟,失掉衡量时间的工具,就觉得夜幕永远不会降临了?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死亡与尸体的感受,在世界最后一天到来前,在审判号角声鸣响前,就见过地狱光景,我们是殉道的艺术家。”
这里也是待不下去了……人类不在爆发中破灭,于是在陨落中消散。好几天我都闭关自守,靠灌安眠药度日。在二层的最后一天无事发生,某位女仆找来要我开镇定剂,说是仅剩的用完了。“谢谢,明年还您。”她走时没头没脑冒了句。
请容我将三楼的样子描摹一下,它显得极不规整,中间空出厅堂,黑绒帷幔挂满壁,天花板中央香烛正哔啵燃烧。房间在四周绕成“口”状集合式公寓那种套间。
倘若不是病人,我会喜欢这里的。身为厌食症患者又偏偏穿红挂绿,突兀的肋排和盆骨令我无端联想到蚂蚁的身材,他们要是膝行,形态也近乎如此吧。更怪异莫过于他们全无抑郁,只是卧床并极不情愿地被输液活下去。连开药都省了的我曾有意无意、试探着询问他们厌食的缘由,只换来一些审题失误:“这是奉献。”——总结,他们的灵魂始终游离在另一个世界。以及不知为何,他们某日会从床上爬起开始为期多天的填鸭式暴食,往后又重返舞台一动不动,如此反复挣扎多次才死去,莫非自虐真有什么快感?

31日早,我第一次在工作时遇见男性员工。我注意到他指尖惨白干瘪,骨节红肿,皲破、裂口都用绷带裹起,饥饿、劳碌分明在他脸边推出两片颧骨。“借一步说话。”他从脖子上摘下备用钥匙打开后门,于是老屋和我的心上都豁然开出个口子——不远处,江两侧的灯影在水中漾开,夏风挟着城市的呼吸掠过耳廓,雨后空气自带一股腐殖土的气息——那时我突然发觉自己宅居太久了。后院种满花草,虞美人的浓重快要揉碎我的眼球。四楼的哥特式窗框又高又窄,一道灰纱掩盖住内景。到天台后,他开始晾晒衣物,床单扑满晨风,飞扬……末了,他背倚铁栏杆向我兜售有神论。“喂,什么时候跟他们学上的?”我不留情面地打断他,“所以你绝食图个什么,等着再过几天一起去挺尸?”“不,医生,您误会了,实在不行算作慢性自杀好了——毕竟这的确难以理解。唔,你在乎过月球和火星上的人什么样子了么?
还有那死星,人流照旧熙熙攘攘,砸掉了闹钟,失掉衡量时间的工具,就觉得夜幕永远不会降临了?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死亡与尸体的感受,在世界最后一天到来前,在审判号角声鸣响前,就见过地狱光景,我们是殉道的艺术家。”

 变小入腹班长作文铁扇公主吧
变小入腹班长作文铁扇公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