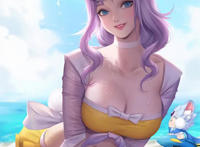【克吧征文】铁屋(3)

这里要提件小事,是关于一楼存酒的。22号晚,我下楼时瞟见一打人立在餐厅里碰着酒杯唱着歌,都是褪去制服一扫委顿,好好修饰了番。可将我惊醒的惊叫又否定了员工娱乐消遣的正当性,虽说双方人数是一半一半,可前者面对申斥很快悻悻散去,自黑暗中传出沉闷、不连贯的啼哭。当问起酒究竟为谁准备,她们煞有介事地回答祭神。
作为精神医生,在这里,我的业务开拓到了侃大山、桌上游戏和音乐鉴赏等等等等,俨然一个居委会大爷。26日下午,我正对一名患者进行催眠治疗,有人拧开收音机企图确认城市广播存亡状况。喇叭里法国圆号的丰腴倾注而出,随后我一阵头昏目眩,脑部简直要从颅腔泄露。乐声忽而澄莹清脆忽而深厚粗重,人们只是咬牙抿嘴、面如死灰,倚着墙或者逃逸,被闻声而来收起天线的护工扯回病房。我尽力直起身走到沙发边躺下,那群退伍兵在在床上或坐或卧,吧嗒吧嗒地抽起烟来,闲手不断摩挲槁枯的双脸。忽而有人叫出声来:“……现在下水道里就有吧,难道我们就不能说出来那天看到了什么,它一口气吞了两个人!”不过在抽泣之前,女仆用酒瓶堵上了他的嘴。往后印象略显含糊,我只记得收好东西早早回到了寝室,连饭都没去吃。还有,睡前我敲响了女孩的门,近乎乞食,索取来一支雪茄,烟雾氤氲中,一股从未有过的舒畅感囊括了全身。

 变小入腹班长作文铁扇公主吧
变小入腹班长作文铁扇公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