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卑与自傲中浮沉(2)
七天憋出六个字来。
但由于自身经历受限(up今年二十岁),很难去理解坐月子这种行为所处的状态,因此带来的共情感就没有“便秘”来得强烈。
小说大抵是一种双向奔赴的创作形式,作者用尽笔墨去描述书中的情节,最直接的期盼是希望看到这段情节的读者,能和创作者一样,产生对应的情绪,“坐月子”如此,“便秘”亦如此,可以说,追求和读者的共情感是小说最初的创作动机。
从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开始,大致就遵循着这样的思路。
《小年》是一部关于童年玩伴和弥补缺失亲情的故事。
男主角捡到天降的玩伴,与其一同成长,在同伴迷失自我后帮助其寻回,最终大团圆结局,这便是小说的主线,支线则是男主角对于父母态度的变化。
正如上文分析,追求共情感是创作的最初动机,这篇小说的共情感营造的并不完美,大致是青春期少年都会YY的美少女玩伴、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缓和等等,但共情感不能局限在人物的感情上,这篇小说的另一个核心是我对于不完美的一种思考,我觉得很有趣,很独特,于是写出来,想要获得读者的赞许,这也是一种对于共情感的简单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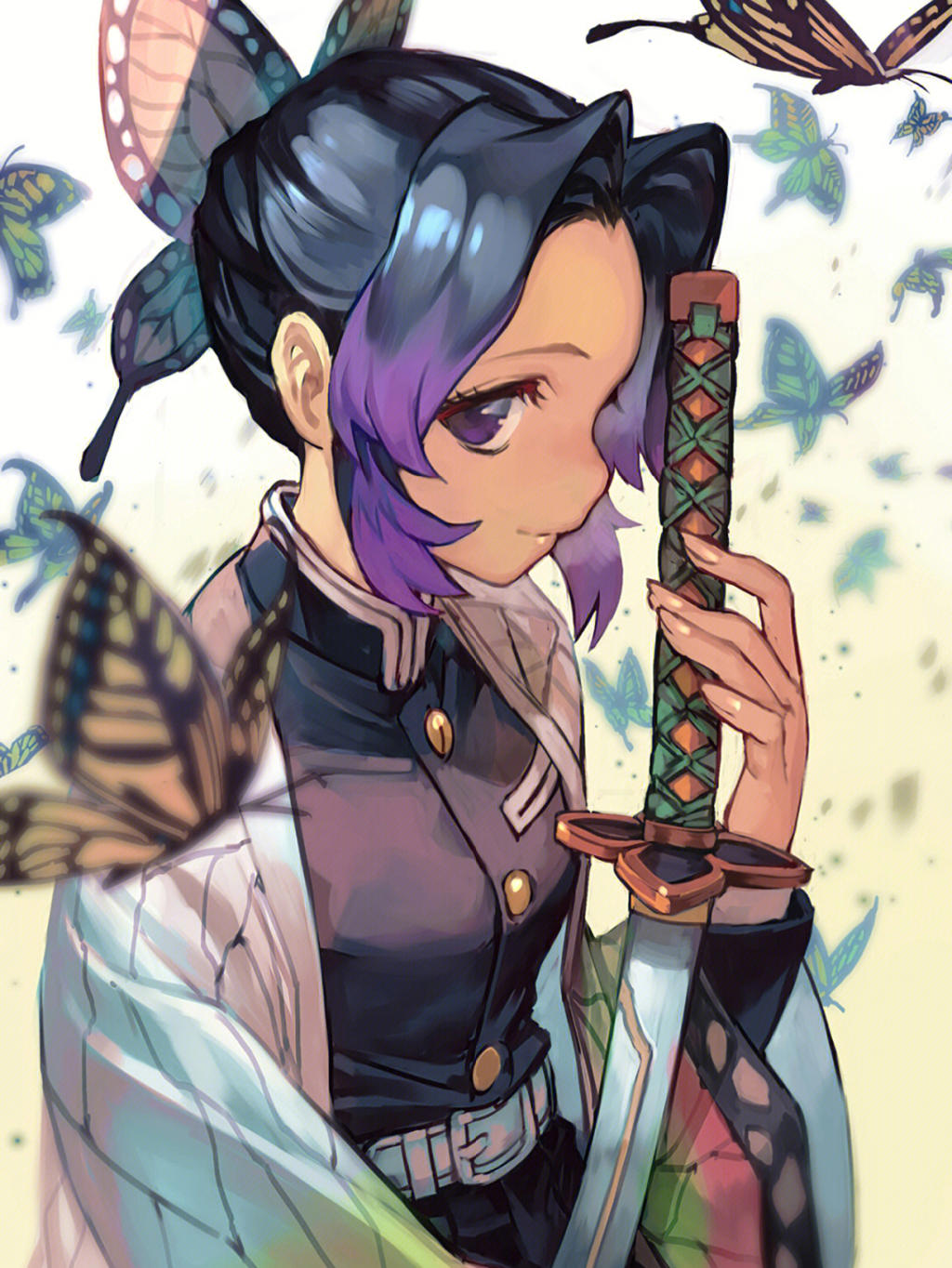
围绕这三个点,我修修补补写出了这篇故事。
在2020年1月18日15时43分写完上传的一刹那,我只觉得自己见证了一位伟大文豪的诞生。
现在的我既对此略感尴尬,又无比的理解这一点——写手在完成作品的那一刹,那种自傲是唯我独尊式的。
这并不是多难理解的事情,写作动机是追求共情,写小说正是写自己共情的事,把自己共情的事亲自码到屏幕上自己去读,那自然是无比共情的了。
脑海中鲜活的情绪在文字中完美的复现,恐怕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事情,更何况这些语句和自己的想法一模一样。
写手对于自己刚刚完成的作品的喜爱大概就是这样。
但事实是怎么样呢?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我的作品并不出色,只是在本人反复观看的过程中,加上了上述的“共情”的滤镜。在自我审视的阅读条件下,创作者有足够多的耐心把自己的作品读完,甚至是在作品的精彩处暗自神伤、自我陶醉一会儿。

 王者荣耀李信自攻自受
王者荣耀李信自攻自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