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钱(8)
只要是死人,就再没人会想着把人救回来。
温文入院的第二天就撑起了自己的身体,按理说,即使是用组织修复剂缝合了断骨和组织,也需要给血管重新蔓延的时间,但温文没有。
温文扶着墙,哒哒地迈着步子就出了自己的病房。
走廊很熟悉,透过围栏看下大厅的场景很熟悉,她于是就在往那边走了五步,就推开了门。
这里只有这一座医院。
她还记得,自己的这间病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那位老人是因为癌症去世的,临死前,她让温文把那些家里孩子给她带的,极其昂贵的水果拿去给她母亲吃。
所以,母亲和Discar的病房,离这里不远。
那里有人,不出所料,她也只是生硬地说了声打扰了,就径直地闯了进去。
她轻嗅着味道。
她抚摸着墙壁。
“请来这里坐下。”
那位女性给她搬了一个椅子,她在察觉到自己打着颤的腿已经不知不觉地脱了力,像只被抽去骨头的羊羔,软绵绵地倒进了椅子。
“很高兴认识您,小姐。”
温文几乎是第一次在母亲死后完成了如此疯狂的倾诉。
那天晚上,点着一个那时已经很罕见的烛火,两个人静静地听着她,讲完了漫长的故事。
从Discar遭遇的意外,到自己的孤苦,再到丢掉的工作,她疯狂地流着泪水,疯狂地挥舞着肢体,疯狂地咒骂着那些杀千刀的司机,老板,路人,疯狂地嘶喊着自己的痴情,绝望,来日方长。
他口头的来日方长,刻骨铭心的来日方长,像火焰下的蜡,不经意间就化掉了,时间就这样,不知觉间便燃尽了。
歇斯底里到了疲累,缺氧带着眼前一阵阵的发黑,没有完全痊愈的身体每一处都嘶哑了,不管是动哪里都只听得见骨节摩擦的生涩声响。
叫伊芙蕾的银发少女眨动着蓝色的瞳子,默默地倾听。
叫因卓的陪护者不断地抛动着手中的一根试管一样的器皿,看着它被抛向空中,液体转过的地方划过磷光,随后落回手中。
“他们说我爱得不够深。”
温文颤动着嘴唇。
“谁。”
“.......朋友。”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足够爱他,Discar绝对不会死。”
温文入院的第二天就撑起了自己的身体,按理说,即使是用组织修复剂缝合了断骨和组织,也需要给血管重新蔓延的时间,但温文没有。
温文扶着墙,哒哒地迈着步子就出了自己的病房。
走廊很熟悉,透过围栏看下大厅的场景很熟悉,她于是就在往那边走了五步,就推开了门。
这里只有这一座医院。
她还记得,自己的这间病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那位老人是因为癌症去世的,临死前,她让温文把那些家里孩子给她带的,极其昂贵的水果拿去给她母亲吃。
所以,母亲和Discar的病房,离这里不远。
那里有人,不出所料,她也只是生硬地说了声打扰了,就径直地闯了进去。
她轻嗅着味道。
她抚摸着墙壁。
“请来这里坐下。”
那位女性给她搬了一个椅子,她在察觉到自己打着颤的腿已经不知不觉地脱了力,像只被抽去骨头的羊羔,软绵绵地倒进了椅子。
“很高兴认识您,小姐。”
温文几乎是第一次在母亲死后完成了如此疯狂的倾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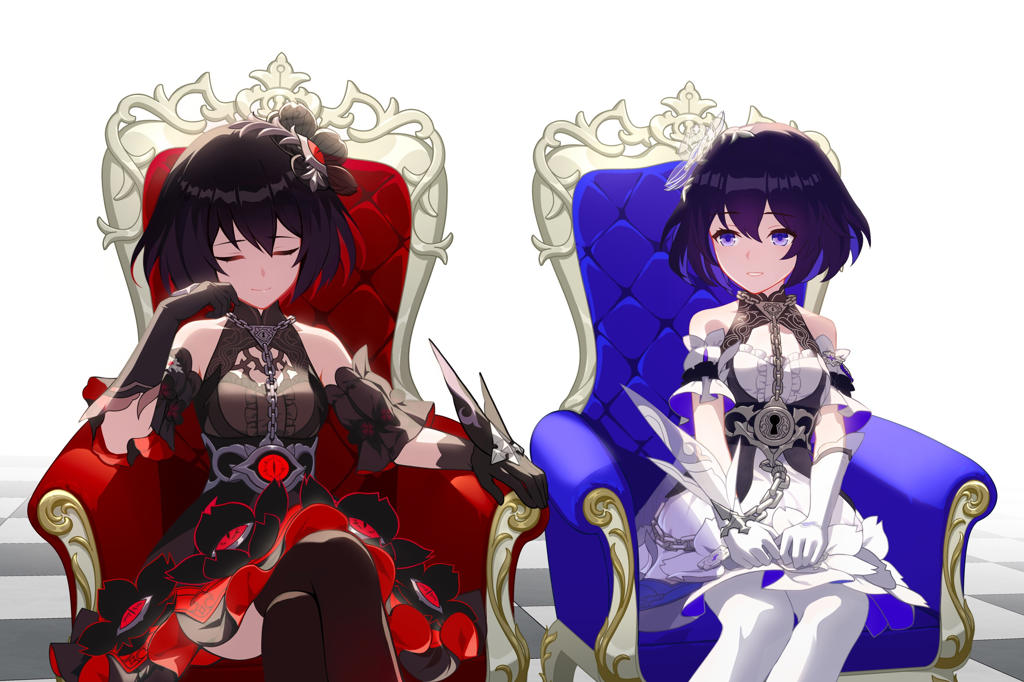
那天晚上,点着一个那时已经很罕见的烛火,两个人静静地听着她,讲完了漫长的故事。
从Discar遭遇的意外,到自己的孤苦,再到丢掉的工作,她疯狂地流着泪水,疯狂地挥舞着肢体,疯狂地咒骂着那些杀千刀的司机,老板,路人,疯狂地嘶喊着自己的痴情,绝望,来日方长。
他口头的来日方长,刻骨铭心的来日方长,像火焰下的蜡,不经意间就化掉了,时间就这样,不知觉间便燃尽了。
歇斯底里到了疲累,缺氧带着眼前一阵阵的发黑,没有完全痊愈的身体每一处都嘶哑了,不管是动哪里都只听得见骨节摩擦的生涩声响。
叫伊芙蕾的银发少女眨动着蓝色的瞳子,默默地倾听。
叫因卓的陪护者不断地抛动着手中的一根试管一样的器皿,看着它被抛向空中,液体转过的地方划过磷光,随后落回手中。
“他们说我爱得不够深。”
温文颤动着嘴唇。
“谁。”
“.......朋友。”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足够爱他,Discar绝对不会死。”

 钱错x滕瑞雨润滑剂车
钱错x滕瑞雨润滑剂车











![[肖钱]给钱钱的一封信(小孔视角)](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313/144205_06790.jpg)
![[肖钱]给钱钱的一封信(小孔视角)](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412/175914_75894.jpg)
![[肖钱]给钱钱的一封信(小孔视角)](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612/151955_4278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