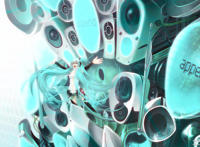文言家史:我的祖父母(第四更:3W5字)[2006- ](17)
壬寅(2022)夏六月二十日,余为祖父母所立之传将已。欲语数话,题以为跋:
盖余所为文者,旨趣大抵有三:或述于前人之事;或思垂文以自见;或以文气相哺。其一之繇,《序》、《表》之述备矣。至于二三,则未为详言,今当自陈。
史公曰:“(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皆“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吾知即出于此。夫人者,必有其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之时;值其思之深、念之切,感伤乎滥、情塞罔极,辄倾一吐而快之,遂心中勃勃有作文意。乃如陈卧子所言,是“(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然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盖结文以抒情,骚客之所同也。于是“寓目写心,因事而作”,“长歌骋其情”。故余所作,既已达心志,则不求于他闻。每所独览,窃惟“心怡即佳篇”。且魏文言:年寿、荣乐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而声名自传于后”。余所为文,未尝不留意于斯。故抒情以自见,而欲诒于子孙后人同观,俾其知我亦为一有血有肉之躯,非独碑上一无情无性之名耳。
若夫文气之相哺,苏辙有言:“文者气之所形。”故孟子善养其浩然之气,其文“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史公行天下,交豪俊以同游,其文“疏荡有奇气”。余固未尝与豪俊携游,亦未见天地之广大;徒困于乡人百里之间,聊语以小家闺作自解。然王国维曰:“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以其“不失赤子之心也”。故余窃谓文章亦可养人之气,即吾文虽不能臻于一流,而余气可以拓之于无穷,然后冀其相哺于万一。盖述文以养气,气以养性,性以养人,此亦辙所谓“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是以不逊而强著文章,即在于兹。以前人之议已尽得吾心,而此又皆余所口未能言,故多引喻,以白余意。非敢掠美。
嗟乎!既述此,文当尽矣。然余终存郁结之意,为仍抱怅然自失之恨。或曰:“人终不脱于一灭,虽宇宙尚有竟时。子所为,述作之值何?”曰:“是如尊言,辄无趣也。夫人活当下,未来之事,所窥至不过二三百年。圣贤虽如此,况于凡人者乎?吾属延祖宗之祀,谋儿孙之后,尽份内之事而已。若夫邈远之世,其壹非余力所及,更自有儿孙谋之,则不与我相干,何消虑也?即与我相干,则我今日述作,是亦尽区区而俾人类终免于绝灭一途。”是以不哀私之力薄,尽精力而著此书,以其值超乎我孤身之值也。尝闻太白言:“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呜呼!其文则傲矣,其志也孤哉!盖世终需此殊调之人,今余为之。
盖余所为文者,旨趣大抵有三:或述于前人之事;或思垂文以自见;或以文气相哺。其一之繇,《序》、《表》之述备矣。至于二三,则未为详言,今当自陈。
史公曰:“(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皆“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吾知即出于此。夫人者,必有其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之时;值其思之深、念之切,感伤乎滥、情塞罔极,辄倾一吐而快之,遂心中勃勃有作文意。乃如陈卧子所言,是“(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然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盖结文以抒情,骚客之所同也。于是“寓目写心,因事而作”,“长歌骋其情”。故余所作,既已达心志,则不求于他闻。每所独览,窃惟“心怡即佳篇”。且魏文言:年寿、荣乐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而声名自传于后”。余所为文,未尝不留意于斯。故抒情以自见,而欲诒于子孙后人同观,俾其知我亦为一有血有肉之躯,非独碑上一无情无性之名耳。
![文言家史:我的祖父母(第四更:3W5字)[2006- ]](https://wimgs.ssjz8.com/upload/2023/0725/154507_23710.jpg)
若夫文气之相哺,苏辙有言:“文者气之所形。”故孟子善养其浩然之气,其文“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史公行天下,交豪俊以同游,其文“疏荡有奇气”。余固未尝与豪俊携游,亦未见天地之广大;徒困于乡人百里之间,聊语以小家闺作自解。然王国维曰:“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以其“不失赤子之心也”。故余窃谓文章亦可养人之气,即吾文虽不能臻于一流,而余气可以拓之于无穷,然后冀其相哺于万一。盖述文以养气,气以养性,性以养人,此亦辙所谓“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是以不逊而强著文章,即在于兹。以前人之议已尽得吾心,而此又皆余所口未能言,故多引喻,以白余意。非敢掠美。
嗟乎!既述此,文当尽矣。然余终存郁结之意,为仍抱怅然自失之恨。或曰:“人终不脱于一灭,虽宇宙尚有竟时。子所为,述作之值何?”曰:“是如尊言,辄无趣也。夫人活当下,未来之事,所窥至不过二三百年。圣贤虽如此,况于凡人者乎?吾属延祖宗之祀,谋儿孙之后,尽份内之事而已。若夫邈远之世,其壹非余力所及,更自有儿孙谋之,则不与我相干,何消虑也?即与我相干,则我今日述作,是亦尽区区而俾人类终免于绝灭一途。”是以不哀私之力薄,尽精力而著此书,以其值超乎我孤身之值也。尝闻太白言:“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呜呼!其文则傲矣,其志也孤哉!盖世终需此殊调之人,今余为之。
![文言家史:我的祖父母(第四更:3W5字)[2006- ]](https://wimgs.ssjz8.com/upload/2023/0731/214457_95577.jpg)
 混乱家长会1―5笔趣阁
混乱家长会1―5笔趣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