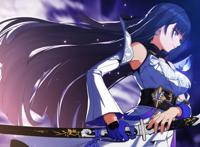第二十二条军规:人们被社会现实任意摆布,却找不到反击的方式(6)
约瑟夫·海勒在小说中设置塔普曼上尉这样一个人物,带有明显的象征色彩。在西方传统中,上帝是超越一切的存在,是所有道德和价值的化身,不仅指引人的精神,也约束人的行为。所以,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人就如同迷途的羔羊,惶惶然不知所以。可是在这本书的世界里,信仰已经不能给人带来拯救,塔普曼上尉非但不能给人以精神和行为上的指导,反而沦落到被卡思卡特上校利用的境地,不得不去念那些他觉得低沉的祈祷文,也不得不违心地向人承诺,人死后上帝会显灵。于是,塔普曼的信仰崩塌了,他发现人的命运被其他难以言状的力量主宰着,上帝非但不能带来拯救,一不小心还成了帮凶。对于西方人来说,再没有什么图景比这样一种现实更加“黑色”了。
在这样一个“黑色”的、精神层面重新回归荒蛮与无序的世界中,卡思卡特和米洛这样百无禁忌的人,显然更容易赢得所谓的成功。而那些有所坚守的人,则难以避免地将死于他们试图坚守的事物。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内特利。内特利出身富贵人家,从小没经历过坎坷,身上有股未经世事的天真劲头。在加入飞行队以后,他爱上了一个意大利当地的妓女,为了能留在飞行大队,他主动要求增加飞行次数,哪怕约塞连跪下来求他,内特利仍然坚持要多飞几次,而且还反过来请求约塞连让卡思卡特上校提高飞行次数。内特利的请愿成了卡思卡特上校的福音,他正愁找不到借口继续提高最低任务的次数,同时他也被到处宣称已经完成飞行任务的约塞连搞得焦头烂额,于是他顺水推舟,在当天傍晚就把飞行次数增加到了八十次。第二天拂晓,德国人的军舰进攻港口,内特利如愿出战,不出所料地葬送了性命。
在所有飞行员中,似乎只有约塞连一个人是清醒的,他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意识到他和他的战友们试图坚守的价值,不管它是上帝、正义还是爱情,在这个世界上都没有生存的空间,他意识到人只有活着才有价值。可是他却不能理性地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因为在一个非理性的、无序的世界中,逻辑、理性和秩序是最没用的东西。一切都是悖论,凡事都自相矛盾,这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本质,也是主宰人命运的那股无以名状的力量。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这么一项规定:凡是疯子就可以申请不用参加飞行任务,但是申请必须本人来提交,而一旦提交申请,就意味着你可以运用理性,意味着你不是疯子,于是也就不符合申请停飞的标准。可以说,这条规定既是阻碍约塞连退役的最大障碍,也是现代人命运最简洁、同时又是最精准的隐喻。对约塞连来说,他处在这样一种情境中:不管他完成了多少次飞行任务,他完成的都是自己的指标,而不是卡思卡特上校的指标,只要他没法证明自己是疯子,他就要一直飞下去,而证明自己是疯子的唯一方式又是清醒地运用理性。
在这样一个“黑色”的、精神层面重新回归荒蛮与无序的世界中,卡思卡特和米洛这样百无禁忌的人,显然更容易赢得所谓的成功。而那些有所坚守的人,则难以避免地将死于他们试图坚守的事物。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内特利。内特利出身富贵人家,从小没经历过坎坷,身上有股未经世事的天真劲头。在加入飞行队以后,他爱上了一个意大利当地的妓女,为了能留在飞行大队,他主动要求增加飞行次数,哪怕约塞连跪下来求他,内特利仍然坚持要多飞几次,而且还反过来请求约塞连让卡思卡特上校提高飞行次数。内特利的请愿成了卡思卡特上校的福音,他正愁找不到借口继续提高最低任务的次数,同时他也被到处宣称已经完成飞行任务的约塞连搞得焦头烂额,于是他顺水推舟,在当天傍晚就把飞行次数增加到了八十次。第二天拂晓,德国人的军舰进攻港口,内特利如愿出战,不出所料地葬送了性命。
在所有飞行员中,似乎只有约塞连一个人是清醒的,他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意识到他和他的战友们试图坚守的价值,不管它是上帝、正义还是爱情,在这个世界上都没有生存的空间,他意识到人只有活着才有价值。可是他却不能理性地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因为在一个非理性的、无序的世界中,逻辑、理性和秩序是最没用的东西。一切都是悖论,凡事都自相矛盾,这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本质,也是主宰人命运的那股无以名状的力量。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这么一项规定:凡是疯子就可以申请不用参加飞行任务,但是申请必须本人来提交,而一旦提交申请,就意味着你可以运用理性,意味着你不是疯子,于是也就不符合申请停飞的标准。可以说,这条规定既是阻碍约塞连退役的最大障碍,也是现代人命运最简洁、同时又是最精准的隐喻。对约塞连来说,他处在这样一种情境中:不管他完成了多少次飞行任务,他完成的都是自己的指标,而不是卡思卡特上校的指标,只要他没法证明自己是疯子,他就要一直飞下去,而证明自己是疯子的唯一方式又是清醒地运用理性。

 all荧关于他们要二胎的方式
all荧关于他们要二胎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