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缄(2)
“申飞.....我称你为申飞,无所谓你怎么称呼我....”他从不叫我的本名,他早已抛去了我的本名,一如他抛去几乎一切他曾经所执拗的,所热爱的,也将努力忘却掉他曾经所执拗的,热爱的。
然而他成功了,成功了一半。
“称呼...”我透着酒劲闷出话来“褒又贬,贬又褒,褒褒贬贬,不知所谓,也无所谓,你不早就厌恶你自己了吗?连殳?”我也同样抛去了他的本名,不过我终究还是“有所谓”地给了他一个称呼,给了他一个有着褒贬的称呼。
“你又何苦来哉?”我又闷出一句。“又有必要吗?还可以再来的不是吗?”
“我只是觉得我自己不配而已。”他跟喝一杯啤一样喝了一杯白。又接着说:
“不那么高尚的说,家里穷,你也知道;那时还病着的老俩口和一个倔弟弟。”他瞅了眼间不容隙的桌上,手指一扬直接把烟蒂扔走,又点上一根华子说:“高尚点说,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说完他狠劲又嘬一口烟:
“然而和平年代的武器嘛....让我在最后抽几口....”这句声音如他口吐的烟一般轻渺,而他看着烟,祭奠着随烟飘逝的,他所热爱的美好的事物,用他已经破陨的心来给予他们最后遗赠的祝福。
然而.....我终于还是皱起眉头了。
“真的有必要这样吗?有这样做的必需吗?你跟你的倔弟弟决裂,把他文稿上稚嫩的希冀撕得粉碎又骂他冷嘲他瞎掰扯什么‘人的渺小’和‘一切虚无’这些自欺欺人的话,你我都知道这些全是骗鬼糊弄人的话!”
“他知道那是骗鬼糊弄人的话,我就是想告诉他得负起责任来了,得好好生活,能让精神有所附丽。”
我低了点头,面孔直朝着他,他的眼瞳收缩了下。
“....那子君呢?”我还是用了她的代称,他清楚。
他张皇了些,原本古井的脸庞终究是颤动了,手攥紧又放松,但这只是一刹那间,便恢复如初。
“我净身出户了。”
“我不是说这个,你自己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自己知道你干了什么!”
“.........”一如他一开始所说,所谓的“不妨害其实际利益的伤害”,便只有从心理层面上了。
“本来都快要结婚了啊!”
“那也....对她来说也会无所谓的,她的亲戚们待她很好,她的家境也殷实,她应该还能承受住,她还会找到她真正的如意郎君......”连殳不想说完了,他猛灌了自己一大口酒。
看来他打听了。
“惟愿我的死亡是自己制定的死刑,我的葬礼上没有人为我哭泣,为我流血,或使人后悔,或使人快意,或为我而在生活中彷徨....”他嘟囔着....
然而他成功了,成功了一半。
“称呼...”我透着酒劲闷出话来“褒又贬,贬又褒,褒褒贬贬,不知所谓,也无所谓,你不早就厌恶你自己了吗?连殳?”我也同样抛去了他的本名,不过我终究还是“有所谓”地给了他一个称呼,给了他一个有着褒贬的称呼。
“你又何苦来哉?”我又闷出一句。“又有必要吗?还可以再来的不是吗?”
“我只是觉得我自己不配而已。”他跟喝一杯啤一样喝了一杯白。又接着说:
“不那么高尚的说,家里穷,你也知道;那时还病着的老俩口和一个倔弟弟。”他瞅了眼间不容隙的桌上,手指一扬直接把烟蒂扔走,又点上一根华子说:“高尚点说,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说完他狠劲又嘬一口烟:
“然而和平年代的武器嘛....让我在最后抽几口....”这句声音如他口吐的烟一般轻渺,而他看着烟,祭奠着随烟飘逝的,他所热爱的美好的事物,用他已经破陨的心来给予他们最后遗赠的祝福。
然而.....我终于还是皱起眉头了。

“真的有必要这样吗?有这样做的必需吗?你跟你的倔弟弟决裂,把他文稿上稚嫩的希冀撕得粉碎又骂他冷嘲他瞎掰扯什么‘人的渺小’和‘一切虚无’这些自欺欺人的话,你我都知道这些全是骗鬼糊弄人的话!”
“他知道那是骗鬼糊弄人的话,我就是想告诉他得负起责任来了,得好好生活,能让精神有所附丽。”
我低了点头,面孔直朝着他,他的眼瞳收缩了下。
“....那子君呢?”我还是用了她的代称,他清楚。
他张皇了些,原本古井的脸庞终究是颤动了,手攥紧又放松,但这只是一刹那间,便恢复如初。
“我净身出户了。”
“我不是说这个,你自己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自己知道你干了什么!”
“.........”一如他一开始所说,所谓的“不妨害其实际利益的伤害”,便只有从心理层面上了。
“本来都快要结婚了啊!”
“那也....对她来说也会无所谓的,她的亲戚们待她很好,她的家境也殷实,她应该还能承受住,她还会找到她真正的如意郎君......”连殳不想说完了,他猛灌了自己一大口酒。
看来他打听了。
“惟愿我的死亡是自己制定的死刑,我的葬礼上没有人为我哭泣,为我流血,或使人后悔,或使人快意,或为我而在生活中彷徨....”他嘟囔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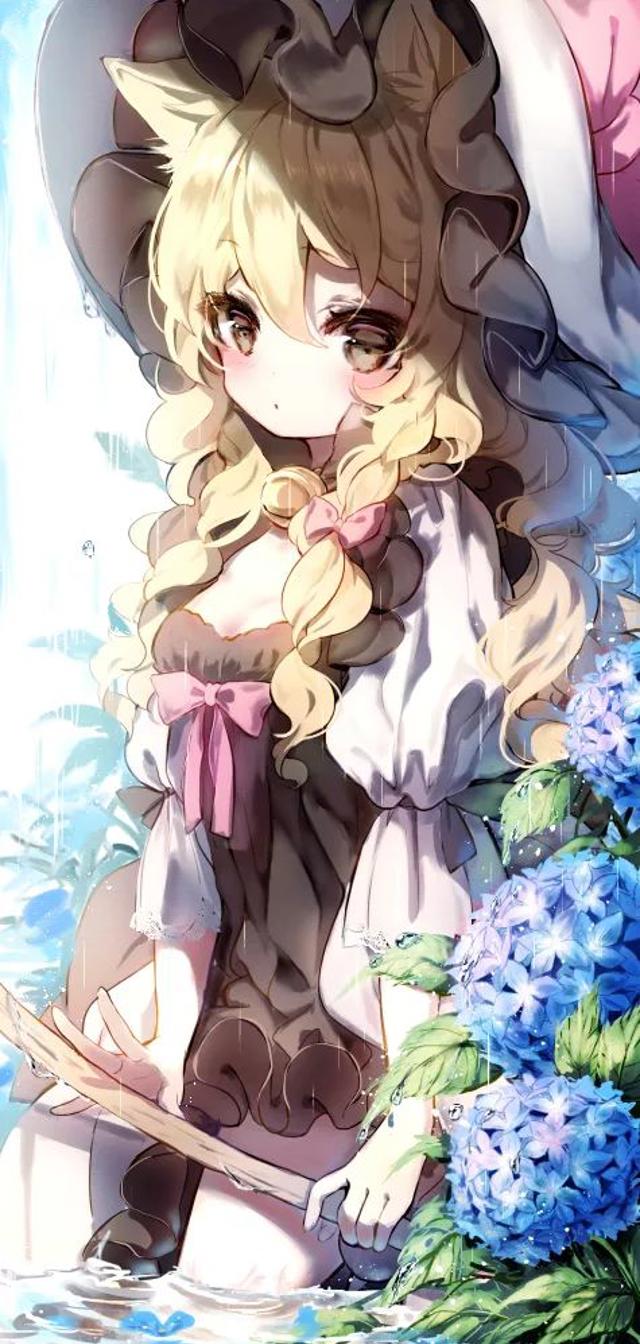
 蓝湛误会魏婴用鞭子抽魏婴的小说
蓝湛误会魏婴用鞭子抽魏婴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