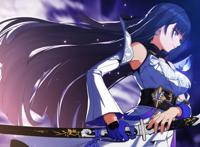一事无成(6)
沉默知道他的下一秒,下一个小时,下一个夜晚干什么,他知道混混课时,混混学分,发发呆,去食堂干饭,干完饭在落日余晖的晚霞之下的操场翠绿的草坪上看他们的貌美纯洁的学姐学妹在跑道上欢声笑语地跑步,她们的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想去知道干净透彻的美貌像极了青春的潮起潮落。观看完青春后,夜晚就悄无声息地降临 ,宿舍里开始亮起一块又一块明亮的电脑屏幕 ,他知道,他该陪着他的LOL了,像无数个熟悉而又往常的夜晚。
可程末不知道下一天,下一个月,下一年将做些什么,他全无规划,也毫无准备,甚至从未思考过自己的人生,他甚至不知道自己选择的专业道路在未来人生中的自己是否会接受。自从进入这个学校的那一刻起,他似乎断了某种脐带,可是又好像手腕又好像扎上了某个吊瓶的输液带,自己不扎,这病就好得慢些,自己扎了痛了,这病又好得快些。输液里存在着自我认识的因子,带他抵抗这种疾病的折磨。18岁以前,他在爸妈姐姐众归所望的一条道路上驰聘飞奔,18岁以后,他像条丢了主人的导盲犬焦急而又慌张地狼奔逐突,他的爸妈姐姐在摆渡到18岁这个港口,送上一条更大更恢宏的泰堪尼克号,就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快乐地和他道别,然后就忙忙碌碌上他们的贼船上去上他们熙熙攘攘的班,他的年纪尚轻的姐姐除此之外还要去应对令她焦头烂额的新婚生活和如临大敌的婆媳关系,每个人都看起来忙碌琐碎而又充实,只有他还在毫无目的地挥霍他的青春,透支他的船票,他也没有成为他曾倾羡过的目标的不羁的杰克.道森,他也没找到令他海风中拥抱和作画的露丝。
程末确实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他也没什么心头所好,于是他成了荒废和虚度的心头所好,他知道夜夜笙歌,知道白日放歌须纵酒,只是青春作伴不好还乡,由此他感受到了一股人生如洪流般盛大的平庸,他感受到了他无法忍受的剧烈的如同烈日灼心的一事无成。
当程末完整而精确像看一条蛇蛇蜕般剖析了自己之后,下课铃声像刺破了爱丽丝梦境般骤然响起,沉默猛然抬头,就好像整个人从深海中望见庞大的鲸落在目不可及的海床上露出如山而又寒冷的骨骸那样般打了个冷颤。狗头老高还在高谈论阔数学家拉格朗日的遗音余韵,清脆的铃声和他手下的学生望向窗外高大的枫树和错落有致的食堂的眼中的渴望都明显阻挡不了他对拉格朗日的推崇至极和侃侃而谈,老高像老鹰抓草原上柔弱的兔子一样低头,眼神点了一下他手中有些老旧年代气息的石英表,顺手推了下无框眼镜,点的时候也不忘分毫不差地加快语速,仿佛要加速进入高潮,老高意味犹尽地谈吐着沉默听不懂的名词和专业术语,他已经有些老态的轮廓和沟壑的脸庞因为他的沉浸的意味犹尽显得红光满面,红光满面地连他顶上稀疏的地中海都凛然地凭空出一股怒发冲冠凭栏处的气质。
老高噼里啪啦只用了五分钟解决了战斗,可能拉格朗日也没想到他可以这么短促而又精髓,老高说完可能有些舌燥,他对同学们例行公事而又和蔼温和地微笑道-作业会在学习通上布置,大家有空做一下提交,下课了,同学们下周一再见-之后,老高拿起他黄铜色前些年学校奖励优秀教师的保温茶杯抿了一口浅褐色的不知名茶水,推了一下他倦怠得有些纠结的眉角,舒缓了一些后,老高精准快速,算无遗策地收拾他的公文包,比他眼下欢愉得如蒙大赦的学生还快,他比学生快人一步、急匆匆地提着公文包走出教室门,麻利地消失在走廊尽头,麻利到看也没看学生一眼多余的眼神一眼,可能老高家里的老婆已经煮好了饭菜在教工宿舍等着他,可能他还有临近期末日渐繁重的会议,可能他还有他上心或不上心的学生作业堆积在案牍上等待他的劳形。或许是老高太经验丰富了吧,他知道有些学生对他的课昏昏欲睡,有些人醍醐灌顶,有些不是聪明也不是喜欢只是习以为常的认真学习的态度聚精会神地听他的课记着笔记,也知道有些人混混,为了几个学分在那故作姿态,实际上内心早已昏聩地与周公梦游,他也知道有些学生不适应他的讲课方式,然后变成不喜欢,最后恨之入骨地咬牙切齿,紧接更难以适应,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可程末不知道下一天,下一个月,下一年将做些什么,他全无规划,也毫无准备,甚至从未思考过自己的人生,他甚至不知道自己选择的专业道路在未来人生中的自己是否会接受。自从进入这个学校的那一刻起,他似乎断了某种脐带,可是又好像手腕又好像扎上了某个吊瓶的输液带,自己不扎,这病就好得慢些,自己扎了痛了,这病又好得快些。输液里存在着自我认识的因子,带他抵抗这种疾病的折磨。18岁以前,他在爸妈姐姐众归所望的一条道路上驰聘飞奔,18岁以后,他像条丢了主人的导盲犬焦急而又慌张地狼奔逐突,他的爸妈姐姐在摆渡到18岁这个港口,送上一条更大更恢宏的泰堪尼克号,就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快乐地和他道别,然后就忙忙碌碌上他们的贼船上去上他们熙熙攘攘的班,他的年纪尚轻的姐姐除此之外还要去应对令她焦头烂额的新婚生活和如临大敌的婆媳关系,每个人都看起来忙碌琐碎而又充实,只有他还在毫无目的地挥霍他的青春,透支他的船票,他也没有成为他曾倾羡过的目标的不羁的杰克.道森,他也没找到令他海风中拥抱和作画的露丝。

程末确实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他也没什么心头所好,于是他成了荒废和虚度的心头所好,他知道夜夜笙歌,知道白日放歌须纵酒,只是青春作伴不好还乡,由此他感受到了一股人生如洪流般盛大的平庸,他感受到了他无法忍受的剧烈的如同烈日灼心的一事无成。
当程末完整而精确像看一条蛇蛇蜕般剖析了自己之后,下课铃声像刺破了爱丽丝梦境般骤然响起,沉默猛然抬头,就好像整个人从深海中望见庞大的鲸落在目不可及的海床上露出如山而又寒冷的骨骸那样般打了个冷颤。狗头老高还在高谈论阔数学家拉格朗日的遗音余韵,清脆的铃声和他手下的学生望向窗外高大的枫树和错落有致的食堂的眼中的渴望都明显阻挡不了他对拉格朗日的推崇至极和侃侃而谈,老高像老鹰抓草原上柔弱的兔子一样低头,眼神点了一下他手中有些老旧年代气息的石英表,顺手推了下无框眼镜,点的时候也不忘分毫不差地加快语速,仿佛要加速进入高潮,老高意味犹尽地谈吐着沉默听不懂的名词和专业术语,他已经有些老态的轮廓和沟壑的脸庞因为他的沉浸的意味犹尽显得红光满面,红光满面地连他顶上稀疏的地中海都凛然地凭空出一股怒发冲冠凭栏处的气质。
老高噼里啪啦只用了五分钟解决了战斗,可能拉格朗日也没想到他可以这么短促而又精髓,老高说完可能有些舌燥,他对同学们例行公事而又和蔼温和地微笑道-作业会在学习通上布置,大家有空做一下提交,下课了,同学们下周一再见-之后,老高拿起他黄铜色前些年学校奖励优秀教师的保温茶杯抿了一口浅褐色的不知名茶水,推了一下他倦怠得有些纠结的眉角,舒缓了一些后,老高精准快速,算无遗策地收拾他的公文包,比他眼下欢愉得如蒙大赦的学生还快,他比学生快人一步、急匆匆地提着公文包走出教室门,麻利地消失在走廊尽头,麻利到看也没看学生一眼多余的眼神一眼,可能老高家里的老婆已经煮好了饭菜在教工宿舍等着他,可能他还有临近期末日渐繁重的会议,可能他还有他上心或不上心的学生作业堆积在案牍上等待他的劳形。或许是老高太经验丰富了吧,他知道有些学生对他的课昏昏欲睡,有些人醍醐灌顶,有些不是聪明也不是喜欢只是习以为常的认真学习的态度聚精会神地听他的课记着笔记,也知道有些人混混,为了几个学分在那故作姿态,实际上内心早已昏聩地与周公梦游,他也知道有些学生不适应他的讲课方式,然后变成不喜欢,最后恨之入骨地咬牙切齿,紧接更难以适应,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无一郎和有一郎搞笑日常
无一郎和有一郎搞笑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