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琥珀(9)
冯子青觉得钱思白演技拙劣,他的表现很刻意,是那种毫不掩饰的刻意。
她给面前的两个男人做了介绍,很明显,两个人并没有要握手的打算。
“去车站吗?一起走吧,顺路。”钱思白没带伞,用外套遮着头很自然地走到了冯子青左手边,她的右手边则是沉默地举着长柄黑伞的孙不平,画面看上去极不和谐。
钱思白与孙不平身量、体型都相仿,只是一个絮絮叨叨、一个沉默寡言,一个替她淋着雨、一个为她撑着伞。
她低着头,看着地上水洼中映出的三条倒影。两个男人的身影在冯子青的眼眸中渐渐变形,变成了极为相似却又截然不同的两个自己,一个撑着伞走在村子里的泥土路上,踢着小石子哼着歌;另一个欢笑着在倾盆大雨中向前飞奔,侧着身子仿佛透过厚重的雨幕能够看清属于自己的未来。
两个都是她,两个都不是她。
她感受着两个男人正在为她暗暗较劲,而她被夹在中间,仿佛某种待价而沽的商品。
当年她喜欢围着长她一岁的二憨哥打转,因为二憨哥是全村知识最渊博的人,看过的连环画最多,能给她讲全本的《杨家将》。
当年她将那个阳光下的笑脸牢牢刻在了心里,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怦然心动的感觉,她鼓足了勇气上去搭讪,知道了这个笑容干净的男生竟是自己的同班同学。
当年她在大头贴背面写下了自己在县城的新住址,可二憨哥从没有给她寄过一封信,她曾经半夜躲在被窝里偷偷哭过好几次,然后便彻底忘记了这件事。
当年夜场话剧散场后,她坐在省话剧院的台阶上看着喷泉出神,钱思白的嘴唇凑近她的耳朵,问她有没有带身份证要不要一起去附近的快捷酒店,她听完笑着反手给了他一耳光。
每个瞬间都被粘稠柔软的树脂包裹,被永久性地悬挂在记忆深处,展览,示众。
原来琥珀是一种惩罚。
她想起当年在省话剧院大门外见过的海报,称赞《琥珀》是“刺穿世俗、直击爱情与灵魂本质”的力作,这种虚饰她向来是不信的。琥珀怎么能刺穿本质呢,琥珀只能是一种包裹,让所有更加本质的东西都潜伏在浓稠的伪装中,看不分明。
她给面前的两个男人做了介绍,很明显,两个人并没有要握手的打算。
“去车站吗?一起走吧,顺路。”钱思白没带伞,用外套遮着头很自然地走到了冯子青左手边,她的右手边则是沉默地举着长柄黑伞的孙不平,画面看上去极不和谐。
钱思白与孙不平身量、体型都相仿,只是一个絮絮叨叨、一个沉默寡言,一个替她淋着雨、一个为她撑着伞。
她低着头,看着地上水洼中映出的三条倒影。两个男人的身影在冯子青的眼眸中渐渐变形,变成了极为相似却又截然不同的两个自己,一个撑着伞走在村子里的泥土路上,踢着小石子哼着歌;另一个欢笑着在倾盆大雨中向前飞奔,侧着身子仿佛透过厚重的雨幕能够看清属于自己的未来。
两个都是她,两个都不是她。
她感受着两个男人正在为她暗暗较劲,而她被夹在中间,仿佛某种待价而沽的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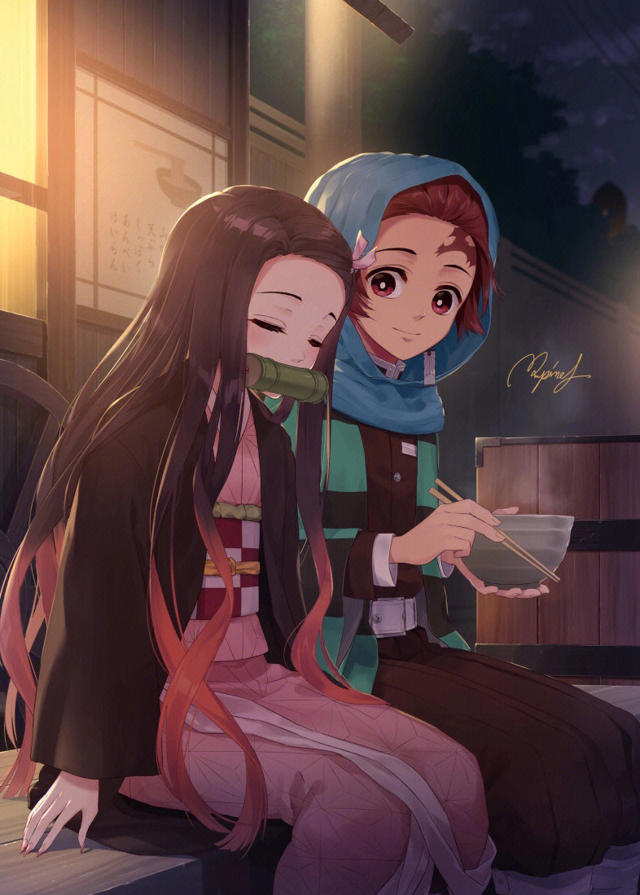
当年她喜欢围着长她一岁的二憨哥打转,因为二憨哥是全村知识最渊博的人,看过的连环画最多,能给她讲全本的《杨家将》。
当年她将那个阳光下的笑脸牢牢刻在了心里,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怦然心动的感觉,她鼓足了勇气上去搭讪,知道了这个笑容干净的男生竟是自己的同班同学。
当年她在大头贴背面写下了自己在县城的新住址,可二憨哥从没有给她寄过一封信,她曾经半夜躲在被窝里偷偷哭过好几次,然后便彻底忘记了这件事。
当年夜场话剧散场后,她坐在省话剧院的台阶上看着喷泉出神,钱思白的嘴唇凑近她的耳朵,问她有没有带身份证要不要一起去附近的快捷酒店,她听完笑着反手给了他一耳光。
每个瞬间都被粘稠柔软的树脂包裹,被永久性地悬挂在记忆深处,展览,示众。
原来琥珀是一种惩罚。
她想起当年在省话剧院大门外见过的海报,称赞《琥珀》是“刺穿世俗、直击爱情与灵魂本质”的力作,这种虚饰她向来是不信的。琥珀怎么能刺穿本质呢,琥珀只能是一种包裹,让所有更加本质的东西都潜伏在浓稠的伪装中,看不分明。

 舰长再也不会原谅女武神
舰长再也不会原谅女武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