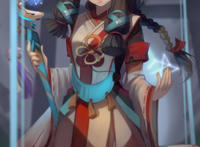锡安无战事 · 第四幕(3)
一个歪歪扭扭的队伍从前线阵地回来,我猜他们是从前线的阵地上修工事回来的倒霉蛋。普宁望着他们出神。我知道他马上就要问一些问题了:“是干啥呢?”他喃喃。
“反坦克壕沟。”我耸耸肩。
“喔。但是……”
“汽车炸弹。”彼得抽着烟,那神态好像那句话不是他说得一样。“不需要炸药,装满煤气罐,车体裹上一层钉子。”
“一公里外都能感觉地在震。你想知道爆炸中心的人最后剩下啥不?”乔立装作兴冲冲的样子,问道。
“不……还是算了吧。”
“咱们那次,是第一次遇见这个手段吧?”伊格纳特的指尖夹着点着的烟,突然说道。
“哪次?”
“那次。你知道的。”
“喔……等下,真是那次吗?”
“千真万确。”
“那次我们是怎么逃出来的啊?”
“天晓得。我只记得我们那次挺惨。”
“是啊,那次,那个谁……那个谁来着?”
伊格纳特开了个坏头,之后就放任我们自己在那胡乱讨论,而一言不发地望穿远方。直到烟卷烫到手指他才注意到,于是把烟叼在嘴上。我们无意间顺出口的某个词可能触发了他的记忆,让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盯着地板上某个东西出神。我们这时却招呼他道:“老伊,走了,你还在磨蹭些啥?”
“哦?哦哦。”他这才嘟囔着,戴上帽子。
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们稍微费了点劲才回到地面上。正赶上那两个散步的人影转悠过来,原来是奥尔德林将军和杰诺特少校——他是我们这片防区的战斗群指挥官。空袭过后,士兵们能见到奥尔德林将军的次数反倒多了起来。我们向防区转移时,能看见他站在路边,望着我们也望着我们身后的瘫痪的装甲车;我们傍晚从地下钻出来去吃饭时,也能看到将军和每次都不一样的某个军官正边走边谈,沿着一条轨道。夕阳把他们拉成了一条剪影。事到如今,大多数的士兵相信这位坚毅的人,因为他纵横一生,鲜有败绩。而自从他空降过来时,这片区域确实在日渐固若金汤。但剩下的人摇摇头,他们并不怀疑自己的指挥官,只是不相信自己的运气。“不管怎样,他只有我们,这六千多人。后方不愿意再往这里调兵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他们这样说。
我们向他们敬了个礼,两人回礼,就继续谈他们的话去了。
第二天一整天都阴沉着天。空气闷闷的,天边在酝酿着一场大雨。我躺在自己的床铺上,看着朋友们凑在一起打牌。帕夫列耶维奇突然急慌慌地跑进门来。
我惊讶地问道:“帕夫列耶维奇,你应该在站岗才是。”
“反坦克壕沟。”我耸耸肩。
“喔。但是……”
“汽车炸弹。”彼得抽着烟,那神态好像那句话不是他说得一样。“不需要炸药,装满煤气罐,车体裹上一层钉子。”
“一公里外都能感觉地在震。你想知道爆炸中心的人最后剩下啥不?”乔立装作兴冲冲的样子,问道。
“不……还是算了吧。”
“咱们那次,是第一次遇见这个手段吧?”伊格纳特的指尖夹着点着的烟,突然说道。
“哪次?”
“那次。你知道的。”
“喔……等下,真是那次吗?”
“千真万确。”
“那次我们是怎么逃出来的啊?”
“天晓得。我只记得我们那次挺惨。”
“是啊,那次,那个谁……那个谁来着?”
伊格纳特开了个坏头,之后就放任我们自己在那胡乱讨论,而一言不发地望穿远方。直到烟卷烫到手指他才注意到,于是把烟叼在嘴上。我们无意间顺出口的某个词可能触发了他的记忆,让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盯着地板上某个东西出神。我们这时却招呼他道:“老伊,走了,你还在磨蹭些啥?”

“哦?哦哦。”他这才嘟囔着,戴上帽子。
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们稍微费了点劲才回到地面上。正赶上那两个散步的人影转悠过来,原来是奥尔德林将军和杰诺特少校——他是我们这片防区的战斗群指挥官。空袭过后,士兵们能见到奥尔德林将军的次数反倒多了起来。我们向防区转移时,能看见他站在路边,望着我们也望着我们身后的瘫痪的装甲车;我们傍晚从地下钻出来去吃饭时,也能看到将军和每次都不一样的某个军官正边走边谈,沿着一条轨道。夕阳把他们拉成了一条剪影。事到如今,大多数的士兵相信这位坚毅的人,因为他纵横一生,鲜有败绩。而自从他空降过来时,这片区域确实在日渐固若金汤。但剩下的人摇摇头,他们并不怀疑自己的指挥官,只是不相信自己的运气。“不管怎样,他只有我们,这六千多人。后方不愿意再往这里调兵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他们这样说。
我们向他们敬了个礼,两人回礼,就继续谈他们的话去了。
第二天一整天都阴沉着天。空气闷闷的,天边在酝酿着一场大雨。我躺在自己的床铺上,看着朋友们凑在一起打牌。帕夫列耶维奇突然急慌慌地跑进门来。
我惊讶地问道:“帕夫列耶维奇,你应该在站岗才是。”

 魏无羡怀孕了沉睡四年
魏无羡怀孕了沉睡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