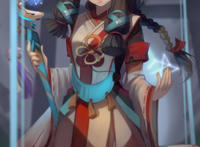锡安无战事 · 第三幕(13)
彼得咕哝道:“我说我怎么总闻到一股臭味。”他转向我,搂着我的脖子:“安德烈小兄弟,你怎么样?你这一天过得如何?”
“不赖。”我戴上帽子,从长椅上起身:“知道吗?我去了趟教堂,出来的时候还从四个混蛋手中解救了一位本地姑娘来着。”
大家一起笑了:“安德烈这小子虽然像头熊,但桃花运一直不错。这可真是怪了。”“你这是英雄救美啦?小心人家打将上门来,我们可不帮你。”“英雄阁下,说说你的感受?”
“爽死啦。”我说。
“啊?这就完啦?”瞪了半天,见我没有说第二句的意思,普宁说。
“我说啥来着?”帕夫列耶维奇讲道:“这小子其实是最闷骚的,有什么都在心里。也许他那兜里还装着信物什么的呢。”
“爽死啦爽死啦爽死啦爽死啦,有完没完?”
“咱们回吧,我感觉我又要吐了……”彼得说。
我们草率地结束了这场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轮休假。走过了很多地方,却好像每次都重复着一无所有地回到军营的这段旅途。又一次,我没办成一件事地逃回到属于我的那摊泥地里去。为什么呢?我仔细地复盘今天经过的一切,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坚持拒绝。朋友们知道我一直很犟,但是在那一刻,我的脑海里被什么占据着,广场上挂着的逃兵,突然涌出来,占满我的脑海。是某样东西触发的,最后我想起来了她眼睛里蕴涵的东西,每一次我在死亡发生之前都从别人脸上看到的东西:她担心我回不来。
这个不确定的念头让我没来由地悲哀。难道现在的氛围真的到了小老百姓都能感到差劲了吗?我嗅嗅空气,都是草香,尘土的味道。但是有一丝……唔,燃烧的橡胶?燃烧的纸?汽油?这些混杂起来的味道。
“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我问我的同伴们。
“我要被酸菜奶油噎死了。”彼得表示。
乔立嗅嗅:“没有什么……不对,好像确实有点什么味道……什么东西烧糊了的味道。”
我们一直在跟着公路走,顺着这条路能一直走回到我们的驻地。但现在我们开始小跑起来,循着那一丝若有若无到渐趋浓烈的枯焦味,我们急于知道答案。
下一个转弯,再下一个……我们来到这条公路的最高点,下面的斜坡一过,就是我们的驻防区域。我们停下来了。
映入眼帘的是火焰,一蹿一丈高,来自于一辆损毁的卡车与上面拉着的货物和驾驶员。我这么说是因为它们一并成为了若干块较大的焦炭,而我们下面的伊索尔达区,半面尽是硝烟,半面为其所熏黑,明火尚有多处。
普宁的声音有些哆嗦:“星条旗打过来了?”
帕夫列耶维奇说:“不,是无人机。”他指着公路上的一个浅浅的坑,里面残留了半截飞翼。他和彼得的酒都醒了。
“不赖。”我戴上帽子,从长椅上起身:“知道吗?我去了趟教堂,出来的时候还从四个混蛋手中解救了一位本地姑娘来着。”
大家一起笑了:“安德烈这小子虽然像头熊,但桃花运一直不错。这可真是怪了。”“你这是英雄救美啦?小心人家打将上门来,我们可不帮你。”“英雄阁下,说说你的感受?”
“爽死啦。”我说。
“啊?这就完啦?”瞪了半天,见我没有说第二句的意思,普宁说。
“我说啥来着?”帕夫列耶维奇讲道:“这小子其实是最闷骚的,有什么都在心里。也许他那兜里还装着信物什么的呢。”
“爽死啦爽死啦爽死啦爽死啦,有完没完?”
“咱们回吧,我感觉我又要吐了……”彼得说。
我们草率地结束了这场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轮休假。走过了很多地方,却好像每次都重复着一无所有地回到军营的这段旅途。又一次,我没办成一件事地逃回到属于我的那摊泥地里去。为什么呢?我仔细地复盘今天经过的一切,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坚持拒绝。朋友们知道我一直很犟,但是在那一刻,我的脑海里被什么占据着,广场上挂着的逃兵,突然涌出来,占满我的脑海。是某样东西触发的,最后我想起来了她眼睛里蕴涵的东西,每一次我在死亡发生之前都从别人脸上看到的东西:她担心我回不来。

这个不确定的念头让我没来由地悲哀。难道现在的氛围真的到了小老百姓都能感到差劲了吗?我嗅嗅空气,都是草香,尘土的味道。但是有一丝……唔,燃烧的橡胶?燃烧的纸?汽油?这些混杂起来的味道。
“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我问我的同伴们。
“我要被酸菜奶油噎死了。”彼得表示。
乔立嗅嗅:“没有什么……不对,好像确实有点什么味道……什么东西烧糊了的味道。”
我们一直在跟着公路走,顺着这条路能一直走回到我们的驻地。但现在我们开始小跑起来,循着那一丝若有若无到渐趋浓烈的枯焦味,我们急于知道答案。
下一个转弯,再下一个……我们来到这条公路的最高点,下面的斜坡一过,就是我们的驻防区域。我们停下来了。
映入眼帘的是火焰,一蹿一丈高,来自于一辆损毁的卡车与上面拉着的货物和驾驶员。我这么说是因为它们一并成为了若干块较大的焦炭,而我们下面的伊索尔达区,半面尽是硝烟,半面为其所熏黑,明火尚有多处。
普宁的声音有些哆嗦:“星条旗打过来了?”
帕夫列耶维奇说:“不,是无人机。”他指着公路上的一个浅浅的坑,里面残留了半截飞翼。他和彼得的酒都醒了。

 第五人格约瑟夫和卡尔的故事
第五人格约瑟夫和卡尔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