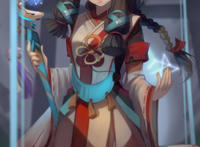锡安无战事 · 第一幕(4)
“在营房里。”我耸耸肩。
“来一首吧,来一首给我们听听。”
“晚上吧,晚上我从医院回来……”
“可惜。”伊格纳特转过去。“医院吵得很,你把手风琴带过去,可能只会被护工赶出来,或者被伤员们的呻吟嚎叫淹没。”
我知道他在打什么鬼主意了。他拿出一副MP5,那是上次战役时他的个人俘获。
“录一首?”我问。
“当然是多录几首。我下午值岗去不了,这高科技玩意放在我这白费了。替我带给卡岑斯基小子。”
除了这件小事外,我们还在去之前把卡岑斯基的东西收拾打包,回去的路上他用得着。这么耽搁了一小晌,你几乎不能相信,他一个在前线打了那么久的兵还有些洁癖,我们在中转站外面又收拾了一下,才进去。
伤兵的中转站应该算是大号的急救站,而非野战医院。这里有经验的医生不多,而且他们大多数时间还被用在挑选可送往后方的伤员这件事上。所以这里一片撤军一样的忙碌,充斥着汗臭、脓血和打翻的石膏味道,消毒液都几乎微不可闻,这味道也就比我们曾经守过的最臭的战壕好一点儿。
帕夫列耶维奇皱皱鼻子:“死人的味道。”
“喂,你少说丧气话……”
我们在一个六人病房里找到了卡岑斯基,他躺在那,看到我们来时,他憔悴的脸上恢复了一些神气,又带有隐藏不住的哀伤无助。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是他放弃了洁癖的习惯,他的床单和被罩一样都是草灰色的,我不敢想象有多少人盖过它,护工到底有没有认真地洗。床头的名片上记着他的全部信息:奥特佳·M·卡岑斯基,AB型血,入院时期、入院原因:子弹击中大腿。
“你看起来好些了。”乔立说道。他把给卡岑斯基的水果放在桌上他能够到的地方,主要是橘子。别的我们既买不到新鲜的,也买不起。
卡岑斯基悲凉地摇了摇头:“我也想这么说,但是……”他下巴点向下身:“他们给我做了截肢。”
很明显,六人病房根本无法好好休息,这不是一位刚刚接受过截肢手术的人应该住的地方。他的气色相当差,和住院前相比,简直像老了二十岁一样,他的一头金发如今黄褐宛如土地,他甚至有了皱纹,难以置信,他和我同龄,才十六岁!无法掩盖的悲凉从他的眼中流出,向这个房间的所有角落。如果没有床头的卡片,我一定会怀疑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卡岑斯基了,他的声音也变得微弱而模糊,一句话:他只剩了半句躯壳躺在这里,而他的灵魂不知道在那里丢掉了大半。
我摇摇头,尽力摆脱掉在我们进来之前护工说得话的影响。“别这样说,很快你就能回家了,然后再不用回来。”
“大部分的你。”索尔参战前是农民,他一向心直口快。“我还得等三四个月才能轮替,到时候我去看你。”
“大部分的我。”卡岑斯基赞同道。他叹口气,“拖着一条腿,我能做什么呢?”
“来一首吧,来一首给我们听听。”
“晚上吧,晚上我从医院回来……”
“可惜。”伊格纳特转过去。“医院吵得很,你把手风琴带过去,可能只会被护工赶出来,或者被伤员们的呻吟嚎叫淹没。”
我知道他在打什么鬼主意了。他拿出一副MP5,那是上次战役时他的个人俘获。
“录一首?”我问。
“当然是多录几首。我下午值岗去不了,这高科技玩意放在我这白费了。替我带给卡岑斯基小子。”
除了这件小事外,我们还在去之前把卡岑斯基的东西收拾打包,回去的路上他用得着。这么耽搁了一小晌,你几乎不能相信,他一个在前线打了那么久的兵还有些洁癖,我们在中转站外面又收拾了一下,才进去。
伤兵的中转站应该算是大号的急救站,而非野战医院。这里有经验的医生不多,而且他们大多数时间还被用在挑选可送往后方的伤员这件事上。所以这里一片撤军一样的忙碌,充斥着汗臭、脓血和打翻的石膏味道,消毒液都几乎微不可闻,这味道也就比我们曾经守过的最臭的战壕好一点儿。
帕夫列耶维奇皱皱鼻子:“死人的味道。”
“喂,你少说丧气话……”
我们在一个六人病房里找到了卡岑斯基,他躺在那,看到我们来时,他憔悴的脸上恢复了一些神气,又带有隐藏不住的哀伤无助。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是他放弃了洁癖的习惯,他的床单和被罩一样都是草灰色的,我不敢想象有多少人盖过它,护工到底有没有认真地洗。床头的名片上记着他的全部信息:奥特佳·M·卡岑斯基,AB型血,入院时期、入院原因:子弹击中大腿。

“你看起来好些了。”乔立说道。他把给卡岑斯基的水果放在桌上他能够到的地方,主要是橘子。别的我们既买不到新鲜的,也买不起。
卡岑斯基悲凉地摇了摇头:“我也想这么说,但是……”他下巴点向下身:“他们给我做了截肢。”
很明显,六人病房根本无法好好休息,这不是一位刚刚接受过截肢手术的人应该住的地方。他的气色相当差,和住院前相比,简直像老了二十岁一样,他的一头金发如今黄褐宛如土地,他甚至有了皱纹,难以置信,他和我同龄,才十六岁!无法掩盖的悲凉从他的眼中流出,向这个房间的所有角落。如果没有床头的卡片,我一定会怀疑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卡岑斯基了,他的声音也变得微弱而模糊,一句话:他只剩了半句躯壳躺在这里,而他的灵魂不知道在那里丢掉了大半。
我摇摇头,尽力摆脱掉在我们进来之前护工说得话的影响。“别这样说,很快你就能回家了,然后再不用回来。”
“大部分的你。”索尔参战前是农民,他一向心直口快。“我还得等三四个月才能轮替,到时候我去看你。”
“大部分的我。”卡岑斯基赞同道。他叹口气,“拖着一条腿,我能做什么呢?”
 王一博做肖战第一次做
王一博做肖战第一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