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楚歌(2)
不疼,他心里这样想。于是他立刻爬起来。可是他的身体却不这样想。手磨破了皮,膝盖摔的生疼。虽然他穿得并不单薄。他想用手安慰一下膝盖,可二者都像是撒娇的孩子一样,合计伙来造反,他蜷缩地蹲了下去。
悲伤像雪崩一样压垮了他,眼睛成了雪水的出口。他摘下眼镜,企图用手堵住,却无济于事。
天阴沉下了,起风了。他的泪水像是绝堤的洪水止不住地流。在风的加持下,脸更容易哭皴。他索性号啕大哭,版预计的不快都吐出来。他张开口,却不知该发出来的声音。怎样才能排泄这些天所有的忧伤?一个答案很快击中了他——楚歌。
楚歌,就是楚地的丧歌——去年的国生就是这样。在靴子白老家,只要有白事,总能听到这样的哭丧歌。他的奶奶就是这方面一把好手。每每逢人过世,她总会适宜的哭一场。当然,农村有些老妪,你会用这种哭腔骂街。在他小时候有些模糊的记忆里,还残存些这类印象。这种现象早已绝迹了。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家里吵了很大的架。奶奶在一个早晨,坐门槛上,哭她命苦。那绵长不绝的哀声,在田野田地间飘荡,魑魅魍魉都听得魂飞魄散。

并没有人教过薛子柏,他也没学过。可楚歌就像溶他的在血液里,此时受了伤,便汩汩地流了出来。我反着记忆中奶的样子,哭诉着心事,用山里的方言:“哎呀呀,我么恁倒霉嘞!我出来找工作,写个小说还遭出版社骗了喂!我如今连房租都交不起,只能睡大街嘞!我路上走的好好的,咋还被人抢包了耶?……”
他的耳朵分明听见的是鬼哭狼嚎,腔不腔调不成调。可洪水行的第一,哪能停住?只能是一泄汪洋,把羞耻心早冲没了影。
眼泪在脸上流淌,并不像冰雨,倒像是岩浆。他的脸红彤彤的,一直红到脖子,连耳朵都像红烧肉一样,只是没有油润的光泽,反而显得粗糙。嗯,比喻成红薯皮来更贴切:他的脸确实皴了。
整条街都被这个二十来岁的孩子吸引。震天的哭声,把窗里的人头都扯到了窗外,诡怪腔调让路人纷纷驻足。走路的、遛狗的,卖东西的!买东西的,有伴儿的、没伴儿的都望着他。悲伤的河流淹没了整条步行街,岸上挤满了围观的人群。
他一直哭着,嘴里响着诡异的楚歌。身边渐渐围出一个好奇的圈。还有人拿出手机拍照,发到网上。他们听不懂他唱的什么玩意儿(但知道肯定不是乞讨),想让见多识广的网友看看。人圈里还混合一个记者,拿着摄像机,他的鼻子闻到了头条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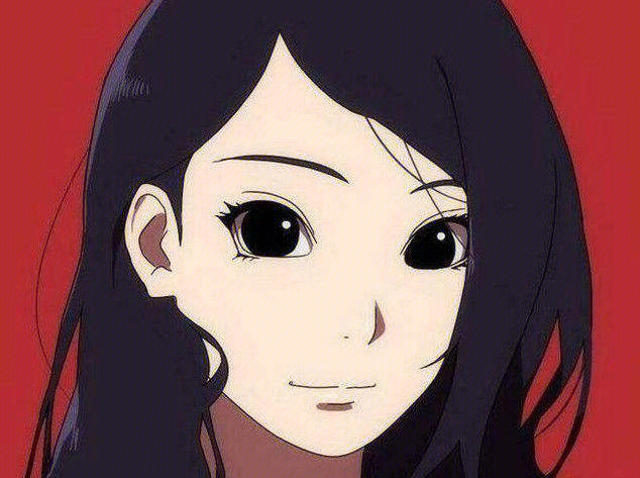
 江停archieve of our own
江停archieve of our o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