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糖纸上的英雄(5)
不知不觉中,我忘却了糖纸上举枪的英雄,转而发现自己身旁那位黝黑的汉子身后,也立着一把无形的,烧着蓝白色天空和海面的枪。
母亲后来离开了她工作二十年的部队大院,那个我生长起来、爬沙坑学打枪的大院,带着我转向更远阔的天地。我在那里读书,读到海明威,与那片广袤无垠、只出现在童话里的海。我依然保持着吃糖的习惯,尽管摸不到那个很少打开的木头抽屉,依旧跑到附近的瓜子店去买糖。
我很少再吃到那种甜腻的花生糖,包装上也没有画着白蓝相间的超级英雄,取而代之的是更接地气的一两颗花生。仔细看过才知道,包装上其实印着五个字:前两个是“花生”,后面还跟着三个“牛乳糖”的字。
至于为什么从前没注意,大抵是不认得,或者只喜欢花生而已。如今看全了名字,欣喜之余,我总摸到胸口左侧的空荡。
我依旧坚持收集糖纸,将它们黏贴在老旧的电话簿后面,一张张铺平,就像铺平我的被子,铺平写字的纸张,铺平木头抽屉上贴着防脏的玻璃纸,铺平一切我已走过或将要走的路。
我却再没见过三叔。
母亲后来也说我好笑。孩子的耳朵听不清话,我以为是“三叔”,还想着有什么血缘关系在其中,却不知她其实喊的是“生叔”。只是老表的口音不分平翘,本就歪读成了“山叔”,再一念快了便成了“三叔”。想来我三叔三叔的叫了快十年,不知三叔他自己,究竟发现了没呢?
多少次曾经吃着宝贵的花生糖,我想起那个暑假的炎热,断电的书报亭,和蝉鸣中一圈一圈缓慢转动的电风扇,拍不完的蚊子。玻璃杯中的茶叶在水中浮动,而后慢慢地沉入茶水,在厚厚的杯底昏睡过去,再不起来。
黝黑的带着伤疤的三叔,漂浮在船上试图击退坏人的男人;那片我或许知道,确切知道方位的祖国的海——在茶叶沉底的一刻糅合在一起,像一只划过天际的水鸟拍打起浪花,飞向望不见尽头的云端,轻轻打湿了我的梦。
那大概是我的童年,也是拥有我童年的三叔。只是那些藏在木头抽屉底部的东西,都随着星斗转移变换。花生糖的香气,飘散在夏夜清爽的风里,送至蓝白相间的远方。
我认识三叔只有十年,他认识我,大概也只有十年。三叔已然老去,不会再记得自己收藏在木头抽屉里的花生牛乳糖。他唯一有印象的,或许只有一枚压箱底的子弹,从童话里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子弹,静静地躺在木头抽屉最里侧的角落,不小心被无知的孩童瞥到一眼。
母亲后来离开了她工作二十年的部队大院,那个我生长起来、爬沙坑学打枪的大院,带着我转向更远阔的天地。我在那里读书,读到海明威,与那片广袤无垠、只出现在童话里的海。我依然保持着吃糖的习惯,尽管摸不到那个很少打开的木头抽屉,依旧跑到附近的瓜子店去买糖。
我很少再吃到那种甜腻的花生糖,包装上也没有画着白蓝相间的超级英雄,取而代之的是更接地气的一两颗花生。仔细看过才知道,包装上其实印着五个字:前两个是“花生”,后面还跟着三个“牛乳糖”的字。
至于为什么从前没注意,大抵是不认得,或者只喜欢花生而已。如今看全了名字,欣喜之余,我总摸到胸口左侧的空荡。
我依旧坚持收集糖纸,将它们黏贴在老旧的电话簿后面,一张张铺平,就像铺平我的被子,铺平写字的纸张,铺平木头抽屉上贴着防脏的玻璃纸,铺平一切我已走过或将要走的路。
我却再没见过三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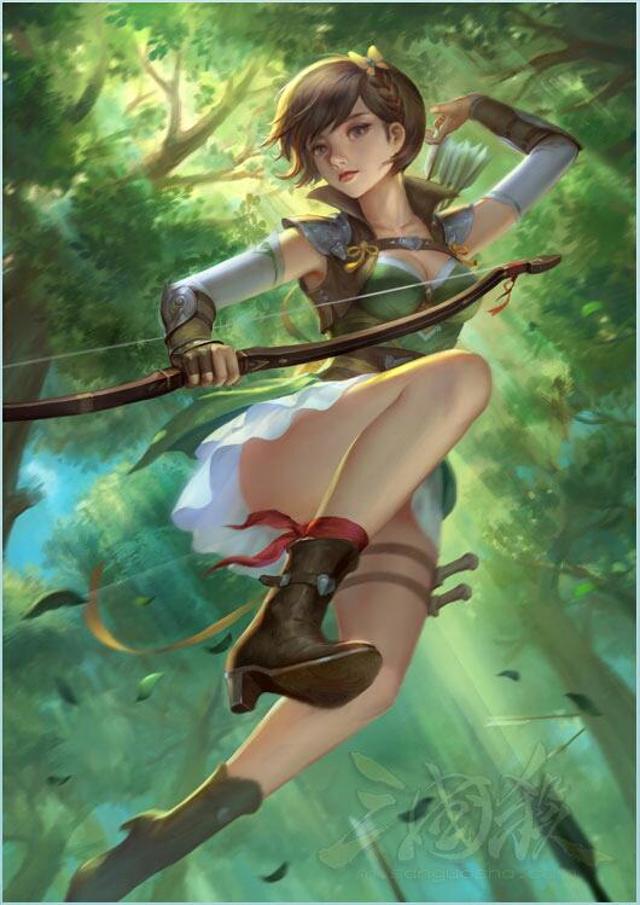
母亲后来也说我好笑。孩子的耳朵听不清话,我以为是“三叔”,还想着有什么血缘关系在其中,却不知她其实喊的是“生叔”。只是老表的口音不分平翘,本就歪读成了“山叔”,再一念快了便成了“三叔”。想来我三叔三叔的叫了快十年,不知三叔他自己,究竟发现了没呢?
多少次曾经吃着宝贵的花生糖,我想起那个暑假的炎热,断电的书报亭,和蝉鸣中一圈一圈缓慢转动的电风扇,拍不完的蚊子。玻璃杯中的茶叶在水中浮动,而后慢慢地沉入茶水,在厚厚的杯底昏睡过去,再不起来。
黝黑的带着伤疤的三叔,漂浮在船上试图击退坏人的男人;那片我或许知道,确切知道方位的祖国的海——在茶叶沉底的一刻糅合在一起,像一只划过天际的水鸟拍打起浪花,飞向望不见尽头的云端,轻轻打湿了我的梦。
那大概是我的童年,也是拥有我童年的三叔。只是那些藏在木头抽屉底部的东西,都随着星斗转移变换。花生糖的香气,飘散在夏夜清爽的风里,送至蓝白相间的远方。
我认识三叔只有十年,他认识我,大概也只有十年。三叔已然老去,不会再记得自己收藏在木头抽屉里的花生牛乳糖。他唯一有印象的,或许只有一枚压箱底的子弹,从童话里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子弹,静静地躺在木头抽屉最里侧的角落,不小心被无知的孩童瞥到一眼。

 王者男英雄的坤巴
王者男英雄的坤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