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耽】琅华映烟寒(3)
戏罢。
柳疏琅透过入相的帘儿向外看,那人早已不见了,心中默叹一声有缘无分。
兴致缺缺卸去妆容,方想出门再试试运气,便被三娘逮了个正着。
“疏琅,你今天怎么回事?”柳姿玉眯瞪一双凤目。
“小姨,今日之事全怪我一时走神。”柳疏琅做了一副低眉顺眼的模样。在至亲面前,他方有几分灵动之气。
“教你唱戏也有十余年了,我可从没见过你犯这种错误!”柳姿玉双手怀抱,旗袍也裹不住徐娘半老的风韵。
“是我不对。”柳疏琅垂眸,不再言语。
“唉,你呀,别像你娘,误了一生。”柳姿玉说罢就走了,留柳疏琅坐着空想。
他本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做父母呵护下的骄子,可父亲和母亲是云泥之别的人,偏是缘分作祟,相遇相知,相爱相离。
父亲终究抛弃了母亲离去,留下母亲身怀六甲,生下了他便难产撒手人寰。父亲也在不久后因过劳而亡。
他不晓得父亲是什么身份,总之母亲在小姨口中,就是不折不扣的秦淮美人,放在民国甚至更远,都是一绝的姿色。
他的百宝匣里一张泛黄的照片,她的母亲穿着绣牡丹的旗袍,正襟危坐地在古镇的相馆照的照片。母亲很美,自己左眼眼尾的那颗泪痣,也随了母亲。至于父亲什么模样,小姨不愿回忆,他亦不想提起。他便从不知父亲什么模样。
好容易理去那些烦扰思绪,方想起那个人,画舫早已停在渡口处,稳稳当当,只是那江水的縠波摇晃着船儿,要唱入夜的渔歌。
换上盘扣麻衣从后台出来,那油纸伞还躺在桌脚,好像等着有缘人寻,那他便有些借口踏着将醺的天色寻人了。
手拿着油纸伞,徘徊在人来人往的夕阳中。却总是瞅不见那抹身影。
“算了,是我自讨无趣。”柳疏琅不再试图探头于一众形形色色人群里。看了看这油纸伞上的一对儿鸳鸯,伸手指了指它们,不免慨叹,“要你这一对儿作甚?该见的终要错过。”
“错过吗?我倒不觉得。”哂笑从身后传来。柳疏琅回头,那人笑意盈盈,眼角眉梢尽是笑意,望着就入了迷。
“你……”
“你好,我叫华琰盛,美玉的琰,盛世的盛。”
“哪个琰?我读书少,见谅。”
“先生语气文绉绉的,倒不像读书少的人。若不介意,我为先生演示一番。”
“哦?如何演示?”柳疏琅难得的好奇起来。
“还请先生伸出手来。”
柳疏琅便乖乖将右手递了出去。
那人大手握住了自己的右手,一阵搔痒从掌心传来,柳疏琅这人最经不得痒的。一阵难以启齿的羞涩和不适又在面上徒生刻意的两抹红云。
柳疏琅透过入相的帘儿向外看,那人早已不见了,心中默叹一声有缘无分。
兴致缺缺卸去妆容,方想出门再试试运气,便被三娘逮了个正着。
“疏琅,你今天怎么回事?”柳姿玉眯瞪一双凤目。
“小姨,今日之事全怪我一时走神。”柳疏琅做了一副低眉顺眼的模样。在至亲面前,他方有几分灵动之气。
“教你唱戏也有十余年了,我可从没见过你犯这种错误!”柳姿玉双手怀抱,旗袍也裹不住徐娘半老的风韵。
“是我不对。”柳疏琅垂眸,不再言语。
“唉,你呀,别像你娘,误了一生。”柳姿玉说罢就走了,留柳疏琅坐着空想。
他本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做父母呵护下的骄子,可父亲和母亲是云泥之别的人,偏是缘分作祟,相遇相知,相爱相离。
父亲终究抛弃了母亲离去,留下母亲身怀六甲,生下了他便难产撒手人寰。父亲也在不久后因过劳而亡。
他不晓得父亲是什么身份,总之母亲在小姨口中,就是不折不扣的秦淮美人,放在民国甚至更远,都是一绝的姿色。
他的百宝匣里一张泛黄的照片,她的母亲穿着绣牡丹的旗袍,正襟危坐地在古镇的相馆照的照片。母亲很美,自己左眼眼尾的那颗泪痣,也随了母亲。至于父亲什么模样,小姨不愿回忆,他亦不想提起。他便从不知父亲什么模样。

好容易理去那些烦扰思绪,方想起那个人,画舫早已停在渡口处,稳稳当当,只是那江水的縠波摇晃着船儿,要唱入夜的渔歌。
换上盘扣麻衣从后台出来,那油纸伞还躺在桌脚,好像等着有缘人寻,那他便有些借口踏着将醺的天色寻人了。
手拿着油纸伞,徘徊在人来人往的夕阳中。却总是瞅不见那抹身影。
“算了,是我自讨无趣。”柳疏琅不再试图探头于一众形形色色人群里。看了看这油纸伞上的一对儿鸳鸯,伸手指了指它们,不免慨叹,“要你这一对儿作甚?该见的终要错过。”
“错过吗?我倒不觉得。”哂笑从身后传来。柳疏琅回头,那人笑意盈盈,眼角眉梢尽是笑意,望着就入了迷。
“你……”
“你好,我叫华琰盛,美玉的琰,盛世的盛。”
“哪个琰?我读书少,见谅。”
“先生语气文绉绉的,倒不像读书少的人。若不介意,我为先生演示一番。”
“哦?如何演示?”柳疏琅难得的好奇起来。
“还请先生伸出手来。”
柳疏琅便乖乖将右手递了出去。
那人大手握住了自己的右手,一阵搔痒从掌心传来,柳疏琅这人最经不得痒的。一阵难以启齿的羞涩和不适又在面上徒生刻意的两抹红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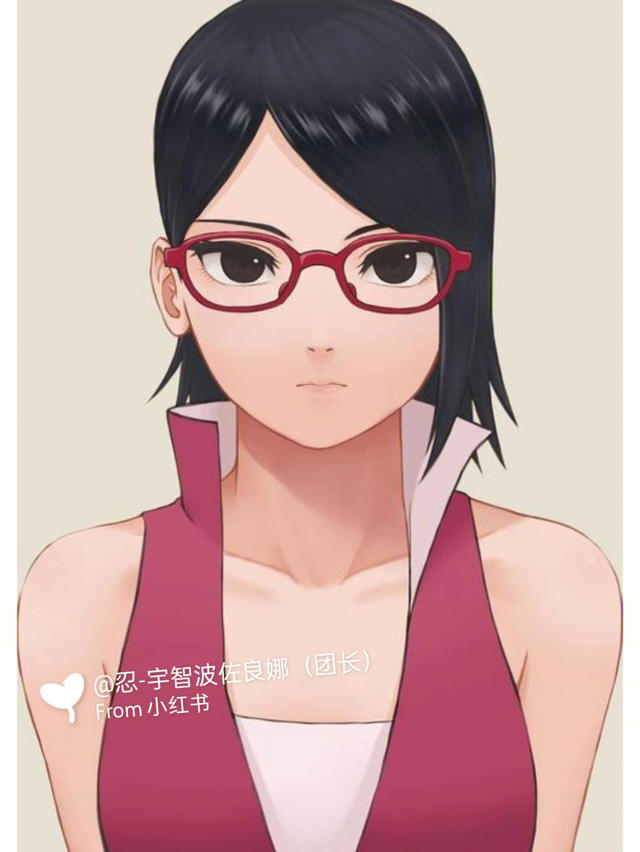
 车原耽
车原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