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土家苗寨的风情画卷一一《表妹堆堆》(4)
在诗意中,我们将世间的美好与温情一一打捞:“龚滩的历史,是一部纤夫和背夫共同书写的长篇,女人就是这部长篇中无穷无尽的标点。只是许多年之后,滩石破碎,木屋下沉,高峡平湖淹埋这些风雨斑驳的故事。只是许多年之后,所有的涛声都成为往事,捣衣声里的爱情成为传说,于是我们开始翻阅古镇”(《老龚滩》)。
在诗意的乡村里,心灵触角会变得极其纤细,耳朵听得到常人听不到的,眼睛看得见常人看不见的:“这几天,我仿佛听见春天的山坡上花开的声音,仿佛听见粉红的桃树下蒿草的呼吸,仿佛听见葫芦湾山坡耕作的歌响。这些声音像风一样染遍了村庄和田野”(《打望一眼葫芦湾》)。在诗意乡村里,我们可以活成一株草木,可以长成一条大河。但是,我们无法在发达的城市里立成一个站牌,活成一个雕塑。在葫芦湾,我们幻化成云,在无边的天空中自由游走,俯瞰世界,笑对人生:“雨天过后的葫芦湾,忙碌得只有空中的白云。来这边山坡堆积,又去那边岭上飞走,棉花似的”(《打望一眼葫芦湾》)。不肯弯腰的只有竹林里破缝而出的嫩竹,白云哗啦啦地压过来,竹节上笋壳脱落开去,离开腰身”(《苗家布鞋》)。而一山一水,常常是启悟我们的哲人:“笔架山在我们这群匆匆过客的眼里,更形似老僧坐禅。
早晚云雾缭绕时,山形隐隐;夏雨空濛后,一身翠绿;或遇朝阳洒落背面,犹如黄金浇铸一般”(《桨声里的酉水河》)。
· 图为老秋湾映像
黄老师笔下的乡村不仅有诗性,也有着灵性与神性。乡村有生命,会生长,也会凋零。当我们呵护他,她长得水灵精灵,并反哺我们:“清清的河水喂养田园,田园喂养村庄”(《歌声飘满南溪河》)。当我们不善待她,她的美丽容颜就将凋零,我们的灵魂之根也将无所归。人与乡村,实际上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江水之岸、巨石之上,野山竹不断在生长,竹林之间,不断有茅屋延伸。茅屋与茅屋中间,向江岸垂落一条石梯,去了江水轰鸣的码头,木船在石梯尽头随波摇摆,远远望去,像古镇呼吸的心脏”(《老龚滩》)。
在诗意的乡村里,心灵触角会变得极其纤细,耳朵听得到常人听不到的,眼睛看得见常人看不见的:“这几天,我仿佛听见春天的山坡上花开的声音,仿佛听见粉红的桃树下蒿草的呼吸,仿佛听见葫芦湾山坡耕作的歌响。这些声音像风一样染遍了村庄和田野”(《打望一眼葫芦湾》)。在诗意乡村里,我们可以活成一株草木,可以长成一条大河。但是,我们无法在发达的城市里立成一个站牌,活成一个雕塑。在葫芦湾,我们幻化成云,在无边的天空中自由游走,俯瞰世界,笑对人生:“雨天过后的葫芦湾,忙碌得只有空中的白云。来这边山坡堆积,又去那边岭上飞走,棉花似的”(《打望一眼葫芦湾》)。不肯弯腰的只有竹林里破缝而出的嫩竹,白云哗啦啦地压过来,竹节上笋壳脱落开去,离开腰身”(《苗家布鞋》)。而一山一水,常常是启悟我们的哲人:“笔架山在我们这群匆匆过客的眼里,更形似老僧坐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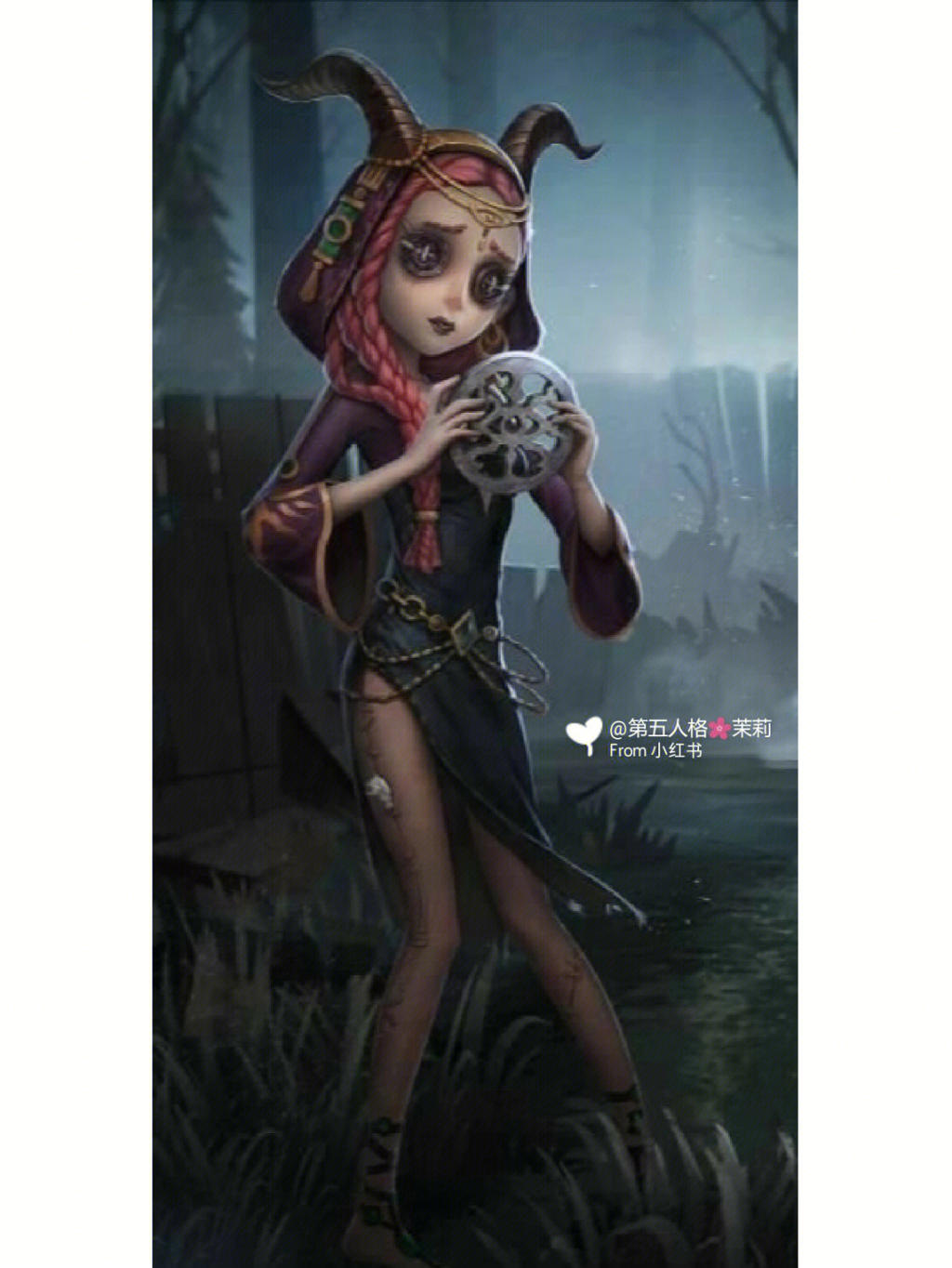
早晚云雾缭绕时,山形隐隐;夏雨空濛后,一身翠绿;或遇朝阳洒落背面,犹如黄金浇铸一般”(《桨声里的酉水河》)。
· 图为老秋湾映像
黄老师笔下的乡村不仅有诗性,也有着灵性与神性。乡村有生命,会生长,也会凋零。当我们呵护他,她长得水灵精灵,并反哺我们:“清清的河水喂养田园,田园喂养村庄”(《歌声飘满南溪河》)。当我们不善待她,她的美丽容颜就将凋零,我们的灵魂之根也将无所归。人与乡村,实际上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江水之岸、巨石之上,野山竹不断在生长,竹林之间,不断有茅屋延伸。茅屋与茅屋中间,向江岸垂落一条石梯,去了江水轰鸣的码头,木船在石梯尽头随波摇摆,远远望去,像古镇呼吸的心脏”(《老龚滩》)。

 一步一步教你画花城
一步一步教你画花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