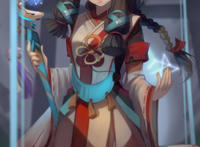来自彼端(3)
荒凉的马场上,一个瘦高的男人在白马的面前注目。他一头栗色的头发有些杂乱,看起来像未经梳理的马鬃一样。他深陷的眼窝里饱含着悲伤和遗憾,干瘦的手指微微颤抖着;马儿躺在地上,四周有它临死前抽搐挣扎的痕迹,它的眼中布满血丝,眼眶也猩红,和男人的眼睛一样。
男人是“根”,是这个马场里负责饲养马和善后工作的人。平时的工作是掏掏马粪,清理马厩,并从上头领来分配好的饲料和培养餐,按时喂给马儿们。剩下的时间,马儿们会被教员们带走训练,他就和同伴们一起清扫马场的卫生。
和他一样的人,在这个马场里一共有六人。
和他一样的人,在这个社会的底层有无数个。
他们都是“根”,没有名字,没有身份。被政府测定为“劣等人种”,在社会中苟延残喘,任由自己的价值被压榨的一干二净。不许繁衍,没有自由;“根”存在的价值,是为了上层人们生活地更加美好。
这里是佛罗里达,是被自由粉饰了无数囚徒的地方。无论是公民,抑或是“根”,每个人都是囚徒。囚禁于欲望,或者是生活。
男人就像马厩里的下等马一样,作为比赛的添头生存在这里。为了衬托上等马的荣光,在沙场拼命狂奔。得不到奖赏也得不到赞誉,他们只为了活命。
“伙伴,你死了;死在了命运之下。你是下等马,是贵人们的玩物,我也一样。”
男人合上了白马的眼睛,将它的遗体搬上了车。
“罗根,别磨磨唧唧的,还有很多地方要打扫呢,这些该死的达尔顿人。”男人的身后传来抱怨声和谩骂声;罗根是他的名字,但这名字仅在“根”之中通用,外面的公民们只称呼他们为“根”,连简简单单加上一个字都不允许。
方才谩骂的人叫苏根,是从墨西哥偷渡过来的。听说佛罗里达遍地黄金,于是上了一艘满载梦的船,却在途中遭遇了一场暴风雨,在摇摆的船上一头装上了桅杆,失去了一只眼睛。
因为这只瞎掉的眼,被政府的优生部认定为“劣等人”,发配到了这个马场里,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四年。
他每天晚上都会喝几罐廉价的啤酒,躺在马厩的草垛里同罗根聊天和吹嘘,说他曾经在墨西哥是多么多么有名的商人,有几百匹布,几百桶油,还有一个葡萄园。可能他真有一个葡萄园,因为他每次说到这里的时候,话总是很多,像一个学者一样。
男人是“根”,是这个马场里负责饲养马和善后工作的人。平时的工作是掏掏马粪,清理马厩,并从上头领来分配好的饲料和培养餐,按时喂给马儿们。剩下的时间,马儿们会被教员们带走训练,他就和同伴们一起清扫马场的卫生。
和他一样的人,在这个马场里一共有六人。
和他一样的人,在这个社会的底层有无数个。
他们都是“根”,没有名字,没有身份。被政府测定为“劣等人种”,在社会中苟延残喘,任由自己的价值被压榨的一干二净。不许繁衍,没有自由;“根”存在的价值,是为了上层人们生活地更加美好。
这里是佛罗里达,是被自由粉饰了无数囚徒的地方。无论是公民,抑或是“根”,每个人都是囚徒。囚禁于欲望,或者是生活。

男人就像马厩里的下等马一样,作为比赛的添头生存在这里。为了衬托上等马的荣光,在沙场拼命狂奔。得不到奖赏也得不到赞誉,他们只为了活命。
“伙伴,你死了;死在了命运之下。你是下等马,是贵人们的玩物,我也一样。”
男人合上了白马的眼睛,将它的遗体搬上了车。
“罗根,别磨磨唧唧的,还有很多地方要打扫呢,这些该死的达尔顿人。”男人的身后传来抱怨声和谩骂声;罗根是他的名字,但这名字仅在“根”之中通用,外面的公民们只称呼他们为“根”,连简简单单加上一个字都不允许。
方才谩骂的人叫苏根,是从墨西哥偷渡过来的。听说佛罗里达遍地黄金,于是上了一艘满载梦的船,却在途中遭遇了一场暴风雨,在摇摆的船上一头装上了桅杆,失去了一只眼睛。
因为这只瞎掉的眼,被政府的优生部认定为“劣等人”,发配到了这个马场里,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四年。
他每天晚上都会喝几罐廉价的啤酒,躺在马厩的草垛里同罗根聊天和吹嘘,说他曾经在墨西哥是多么多么有名的商人,有几百匹布,几百桶油,还有一个葡萄园。可能他真有一个葡萄园,因为他每次说到这里的时候,话总是很多,像一个学者一样。

 writeas前端被堵
writeas前端被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