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锤:我,奥格尼斯。——你好,第四十三千年。(10)
世间万象皆被剥去了色彩,变得光怪陆离,充斥着无法言说的荒诞畸变,就连那站在众人尸骸旁的行凶丑类也仿佛被剥出一层外壳,暴露出更加虚伪丑恶的本质。
阳光,不可名状者的獠牙。
清风,刀锋般恶意具现而出的诡谲腕足。
罪孽、妄念、背叛、谎言、虚伪、傲慢…
还要寻甚炼狱?
人世即炼狱。
明悟即下,又生异象。
一线光自突兀出现在半空的虚掩门扉中透出,映在教士身上,似乎伸出手便可触及,推门而入,迈开腿,即能拾阶而上,步入彼方。
怎奈何…
门上的风铃一响再响。
急促、坚决、不谅人心。
从废墟中醒来,扬-胡斯从未如此刻一般怨恨帝皇的强硬刻薄,方才一道灵能波动掠过大地,为已死的活尸送上帝皇的慈悲,却给弥留之际的将死未死者打上了一针强心剂…他知道是奥格尼斯来了,他一万个不想知道却还是知道了。
一直等到那股悲怆的心能散去,想是那人走了,他才站起身来。
主教的高帽已经和花白的头发一同烧成了灰,长袍则熔结在烧伤的皮肤上,再也揭不下来,他就这么站在裂口纵横的地面上,看着充斥灰烬的稀薄空气凌空聚起一道黑灰的柱,向着人工穹顶上的缝隙钻去,伴着细脆的抽气声,消失在站点外的虚无真空中。
他知道,斯奎克二十七号站点,没了。
他不怨身为帝皇先知的奥格尼斯姗姗来迟,他只怨那人怎么不来的再晚些。
把自己叫回来干嘛啊!
扬胡斯踢了踢脚边的焦尸,用仅剩的右眼往远处望,似乎在找自己被迸溅的陶钢片带走的左脸,徒劳无功。
突然,一声轻微至极的呼救声在他的脚边的瓦砾下面响起——如果火没被刚刚来收尸的人扑灭,这人声必不能透过火烧的噼啪声传出来…痛呼打断了老教士的思绪和迷茫,他一番探察,确定了位置后便用最快的速度向距他百步开外的挖掘机冲去。
“希望能用。”他念叨着。
………………………………
“能感化最好。”
“感化不了,火化次之。”
怜悯是有疏离感的情绪,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安然带来的余裕——你看着战报,遥想被卷入战事的平民的惨状,你当然可以悲天悯人,但身处无间的人们心中只有无光暗夜般无边际的惶恐和神经质的悚然。
他们怕。理所应当。
我自知并非什么圣徒,也不是所谓伟大之人。怜悯?也许有吧,但定然不占此刻心思的千百之一…所以我害怕,怕有朝一日,自己颈上的大好头颅也叫人摘了去,开瓢儿搓捻儿,点天灯!!
阳光,不可名状者的獠牙。
清风,刀锋般恶意具现而出的诡谲腕足。
罪孽、妄念、背叛、谎言、虚伪、傲慢…
还要寻甚炼狱?
人世即炼狱。
明悟即下,又生异象。
一线光自突兀出现在半空的虚掩门扉中透出,映在教士身上,似乎伸出手便可触及,推门而入,迈开腿,即能拾阶而上,步入彼方。
怎奈何…
门上的风铃一响再响。
急促、坚决、不谅人心。
从废墟中醒来,扬-胡斯从未如此刻一般怨恨帝皇的强硬刻薄,方才一道灵能波动掠过大地,为已死的活尸送上帝皇的慈悲,却给弥留之际的将死未死者打上了一针强心剂…他知道是奥格尼斯来了,他一万个不想知道却还是知道了。
一直等到那股悲怆的心能散去,想是那人走了,他才站起身来。
主教的高帽已经和花白的头发一同烧成了灰,长袍则熔结在烧伤的皮肤上,再也揭不下来,他就这么站在裂口纵横的地面上,看着充斥灰烬的稀薄空气凌空聚起一道黑灰的柱,向着人工穹顶上的缝隙钻去,伴着细脆的抽气声,消失在站点外的虚无真空中。

他知道,斯奎克二十七号站点,没了。
他不怨身为帝皇先知的奥格尼斯姗姗来迟,他只怨那人怎么不来的再晚些。
把自己叫回来干嘛啊!
扬胡斯踢了踢脚边的焦尸,用仅剩的右眼往远处望,似乎在找自己被迸溅的陶钢片带走的左脸,徒劳无功。
突然,一声轻微至极的呼救声在他的脚边的瓦砾下面响起——如果火没被刚刚来收尸的人扑灭,这人声必不能透过火烧的噼啪声传出来…痛呼打断了老教士的思绪和迷茫,他一番探察,确定了位置后便用最快的速度向距他百步开外的挖掘机冲去。
“希望能用。”他念叨着。
………………………………
“能感化最好。”
“感化不了,火化次之。”
怜悯是有疏离感的情绪,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安然带来的余裕——你看着战报,遥想被卷入战事的平民的惨状,你当然可以悲天悯人,但身处无间的人们心中只有无光暗夜般无边际的惶恐和神经质的悚然。
他们怕。理所应当。
我自知并非什么圣徒,也不是所谓伟大之人。怜悯?也许有吧,但定然不占此刻心思的千百之一…所以我害怕,怕有朝一日,自己颈上的大好头颅也叫人摘了去,开瓢儿搓捻儿,点天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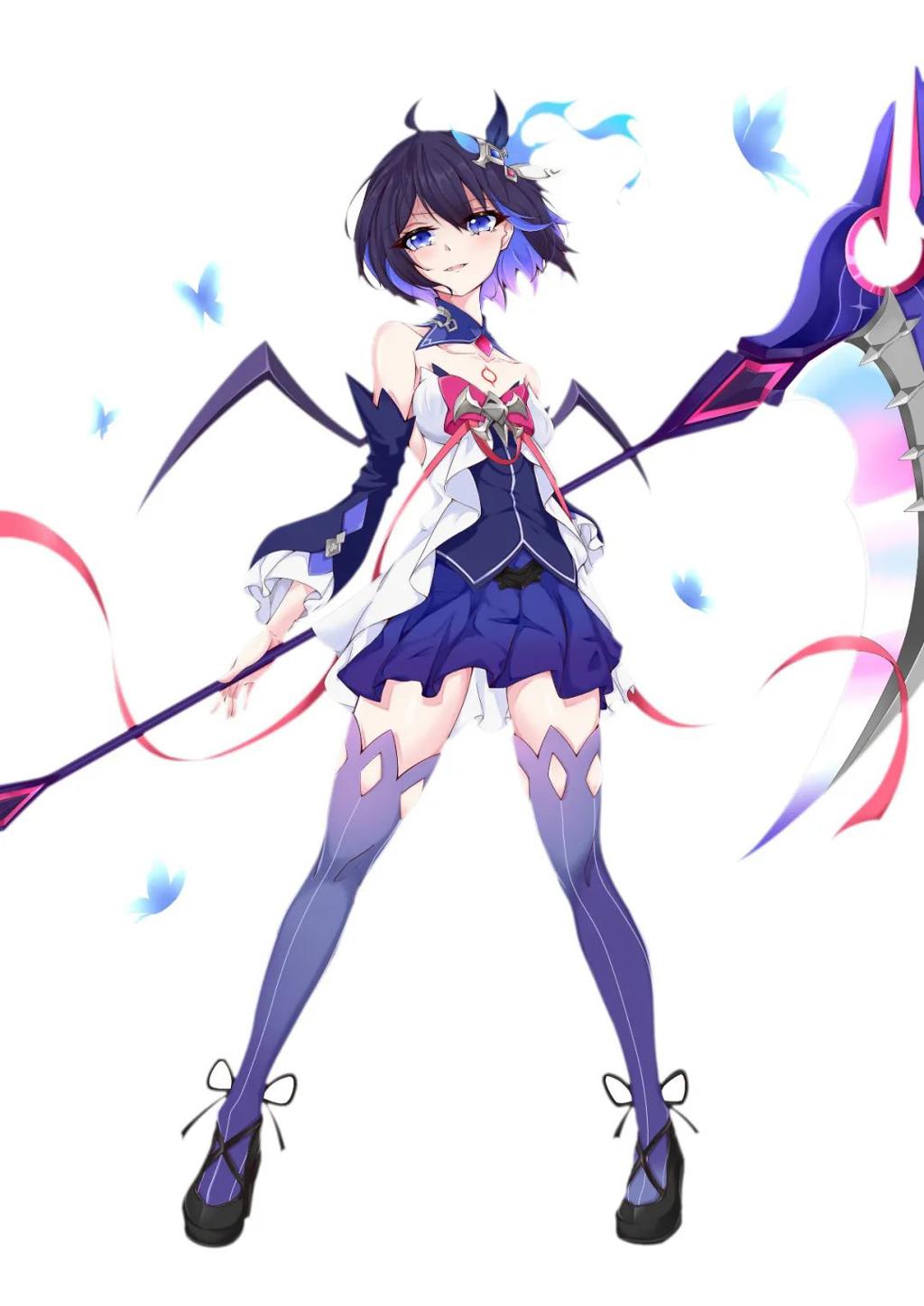
 第五人格小女孩×奥尔菲斯车
第五人格小女孩×奥尔菲斯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