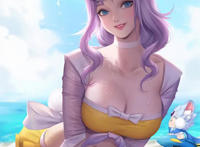春去春来(7)
和他这个妖物,不该有什么牵扯,又能有什么牵扯?
不知多久后,园外的说话声都听不见了,只剩他立在园中,怔怔地,痴痴地,出了神。
世上的事往往不遂人愿,有些人,你千方百计想见她一面时她不出现;等不想见了,她又自动冒出来。几天后的夜里阮卿言来了,和之前每一次一样来得突然,来了就在园子里转悠了半天,末了皱着眉说:“我怎么觉得你这里有点不对?”
他躺在树杈上冷冷地看着她,好半天才说:“我要走了。”
他答应了赤霞子随他去修道,赤霞子要做法打破方丈设下的法印,于是对园中花草树木的格局做了些变化。
“你要走?”阮卿言很吃惊,“去哪里?”
“不用你操心,”他笑了笑,“你要嫁人了,别再管我这妖物的死活!”
这话里赌气的意味不可说不明显,阮卿言初时惊讶,细想一下又笑起来:“洛尘,你这是在吃醋吗?”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他几乎是扑上去恶狠狠地大喊,“我迟早与天地同寿,你一个小小的凡人算得了什么!”
不知多久后,园外的说话声都听不见了,只剩他立在园中,怔怔地,痴痴地,出了神。
世上的事往往不遂人愿,有些人,你千方百计想见她一面时她不出现;等不想见了,她又自动冒出来。几天后的夜里阮卿言来了,和之前每一次一样来得突然,来了就在园子里转悠了半天,末了皱着眉说:“我怎么觉得你这里有点不对?”
他躺在树杈上冷冷地看着她,好半天才说:“我要走了。”

他答应了赤霞子随他去修道,赤霞子要做法打破方丈设下的法印,于是对园中花草树木的格局做了些变化。
“你要走?”阮卿言很吃惊,“去哪里?”
“不用你操心,”他笑了笑,“你要嫁人了,别再管我这妖物的死活!”
这话里赌气的意味不可说不明显,阮卿言初时惊讶,细想一下又笑起来:“洛尘,你这是在吃醋吗?”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他几乎是扑上去恶狠狠地大喊,“我迟早与天地同寿,你一个小小的凡人算得了什么!”

 双璧羡吹皱一池春水04
双璧羡吹皱一池春水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