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方舟】旧垒(10)
我曾问他,我们是否能出去看看,他说,我们只是弄臣,弄臣不应该在主人不允许时离开宫殿,我说,那您可以去找帕夏吗?他说,他找不到帕夏。
他并没有说谎,我们的帕夏只有在她迎接喜讯或颁布法令时现身,其他时候,她可以是一口锅,一张梳妆台,一盆花或是一条汗津津的飘扬在阳台上的衬衫。我们曾经在秋海棠的露珠上看到她木香花般沉重的倒影,在乐队排练室听到她岩石般沉闷的掌声,后厨的仆从和我说,他们经常在午夜听到她咀嚼牛骨的岩石崩裂声,而在两个小时前他们刚刚为她送上一餐车睡前甜点;花匠们和我说,他们在晚上七点的阴凉中,窥见她陶瓷般的手指抚过海棠叶子,翠意笼盖薄雾,由此隔绝了晒伤;驯兽师们和我说,她羽毛油亮长喙金黄的老鹰挣开铁链在吊灯上安家,于是那忧郁沼泽的目光开始游离在象牙长墙的每一处,在人们的午夜私语中,正是她透过爱宠尿液色眼眸的注视烤焦了那对恋人,枭首了那个侍从,外交与军备大臣,不过是她灵魂的碎片罢了。
她对此不解释也不反驳,但她确确实实地听到了,因为说出这些话的人,在第二天夜晚就会和昨夜的伙伴饱饮一壶不知何处来的葡萄酒,一起用蒙着薄雾的叶片割脉,一起于太阳升起的前一刻钟准时准点流光血液,她干雷暴,干木屑与湿木香花的气息因混合了血腥气而变得愈发复杂,不可捉摸,而她母牛般粗厚的呼吸声也因此变得更加厚重,深沉,排山倒海,连我的先知父亲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能在每一夜因她的呼吸而摇晃的星光下感慨,这是神迹。
进入宫廷的第三个秋天,也就是她在宫廷聚会时给我宝石的那段日子里,我成为了下人们的王,而我的父亲却牵着母亲的手,走上了那条铺满秋叶的小径。他在预言时咳血,在宴会上呕吐,大人物们称他为伟大的孕妇,因为他们坚信他那蛙般光滑平实的腹下正孕育着祖国的未来,因此任他被源石折磨得反胃却不给他体检,看着他痛苦地抓挠喉咙却高声说那是神用人的声带宣告命运的前奏,在夏日夜燕的扑翼声中,他胸前别着十颗忠诚勋章,在尼龙吊床上闭着眼对我说,孩子,我好像要死了,你听,死神在窗外游荡呢,而这时我才体验到了他面对冥河中渐行渐远的母亲时的无力感,只能说,这座宅邸里要死的人太多了,还轮不到您父亲。
他又听了三个月我的安慰,并在最后三个月中说光了自己一生中所能说的一切话语,三天,一个星期,四个月,五年,十年,他的灵魂与预言一同浮泛在未来的长河,迷失在天空海洋的碧蓝与夜的墨黑里,它本寄生于他自己的声音,可因为他已开始了对命运赎罪性质的失语,只能靠着他的血脉我的音色才能苟活于世。但有一天,我忙于应付下人却忘了和他说话,于是他疲惫的魂灵就呆在那些香樟树和镜面长廊,呆在火车车轮与铁轨下,被源石压成了一叠明信片。
他并没有说谎,我们的帕夏只有在她迎接喜讯或颁布法令时现身,其他时候,她可以是一口锅,一张梳妆台,一盆花或是一条汗津津的飘扬在阳台上的衬衫。我们曾经在秋海棠的露珠上看到她木香花般沉重的倒影,在乐队排练室听到她岩石般沉闷的掌声,后厨的仆从和我说,他们经常在午夜听到她咀嚼牛骨的岩石崩裂声,而在两个小时前他们刚刚为她送上一餐车睡前甜点;花匠们和我说,他们在晚上七点的阴凉中,窥见她陶瓷般的手指抚过海棠叶子,翠意笼盖薄雾,由此隔绝了晒伤;驯兽师们和我说,她羽毛油亮长喙金黄的老鹰挣开铁链在吊灯上安家,于是那忧郁沼泽的目光开始游离在象牙长墙的每一处,在人们的午夜私语中,正是她透过爱宠尿液色眼眸的注视烤焦了那对恋人,枭首了那个侍从,外交与军备大臣,不过是她灵魂的碎片罢了。
她对此不解释也不反驳,但她确确实实地听到了,因为说出这些话的人,在第二天夜晚就会和昨夜的伙伴饱饮一壶不知何处来的葡萄酒,一起用蒙着薄雾的叶片割脉,一起于太阳升起的前一刻钟准时准点流光血液,她干雷暴,干木屑与湿木香花的气息因混合了血腥气而变得愈发复杂,不可捉摸,而她母牛般粗厚的呼吸声也因此变得更加厚重,深沉,排山倒海,连我的先知父亲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能在每一夜因她的呼吸而摇晃的星光下感慨,这是神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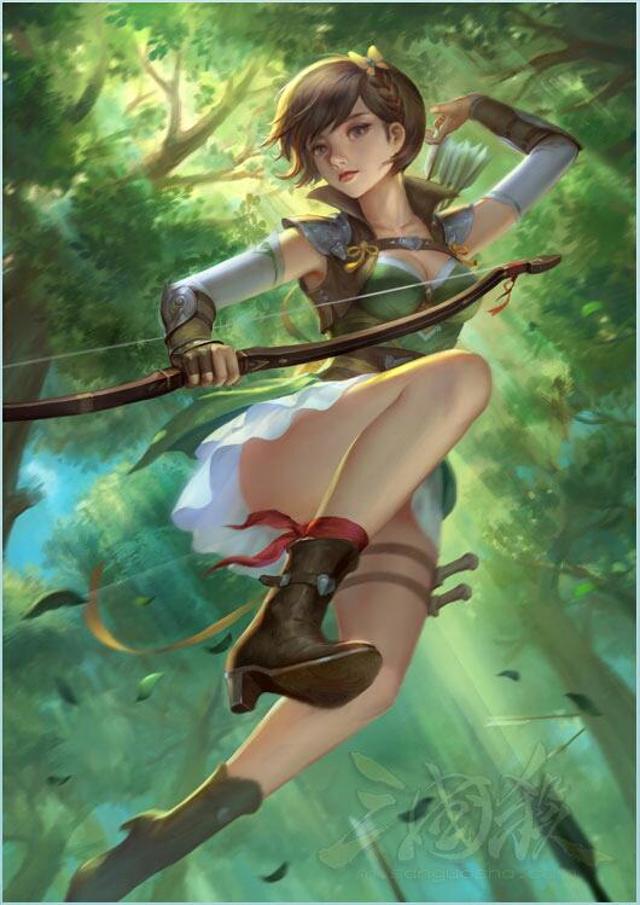
进入宫廷的第三个秋天,也就是她在宫廷聚会时给我宝石的那段日子里,我成为了下人们的王,而我的父亲却牵着母亲的手,走上了那条铺满秋叶的小径。他在预言时咳血,在宴会上呕吐,大人物们称他为伟大的孕妇,因为他们坚信他那蛙般光滑平实的腹下正孕育着祖国的未来,因此任他被源石折磨得反胃却不给他体检,看着他痛苦地抓挠喉咙却高声说那是神用人的声带宣告命运的前奏,在夏日夜燕的扑翼声中,他胸前别着十颗忠诚勋章,在尼龙吊床上闭着眼对我说,孩子,我好像要死了,你听,死神在窗外游荡呢,而这时我才体验到了他面对冥河中渐行渐远的母亲时的无力感,只能说,这座宅邸里要死的人太多了,还轮不到您父亲。
他又听了三个月我的安慰,并在最后三个月中说光了自己一生中所能说的一切话语,三天,一个星期,四个月,五年,十年,他的灵魂与预言一同浮泛在未来的长河,迷失在天空海洋的碧蓝与夜的墨黑里,它本寄生于他自己的声音,可因为他已开始了对命运赎罪性质的失语,只能靠着他的血脉我的音色才能苟活于世。但有一天,我忙于应付下人却忘了和他说话,于是他疲惫的魂灵就呆在那些香樟树和镜面长廊,呆在火车车轮与铁轨下,被源石压成了一叠明信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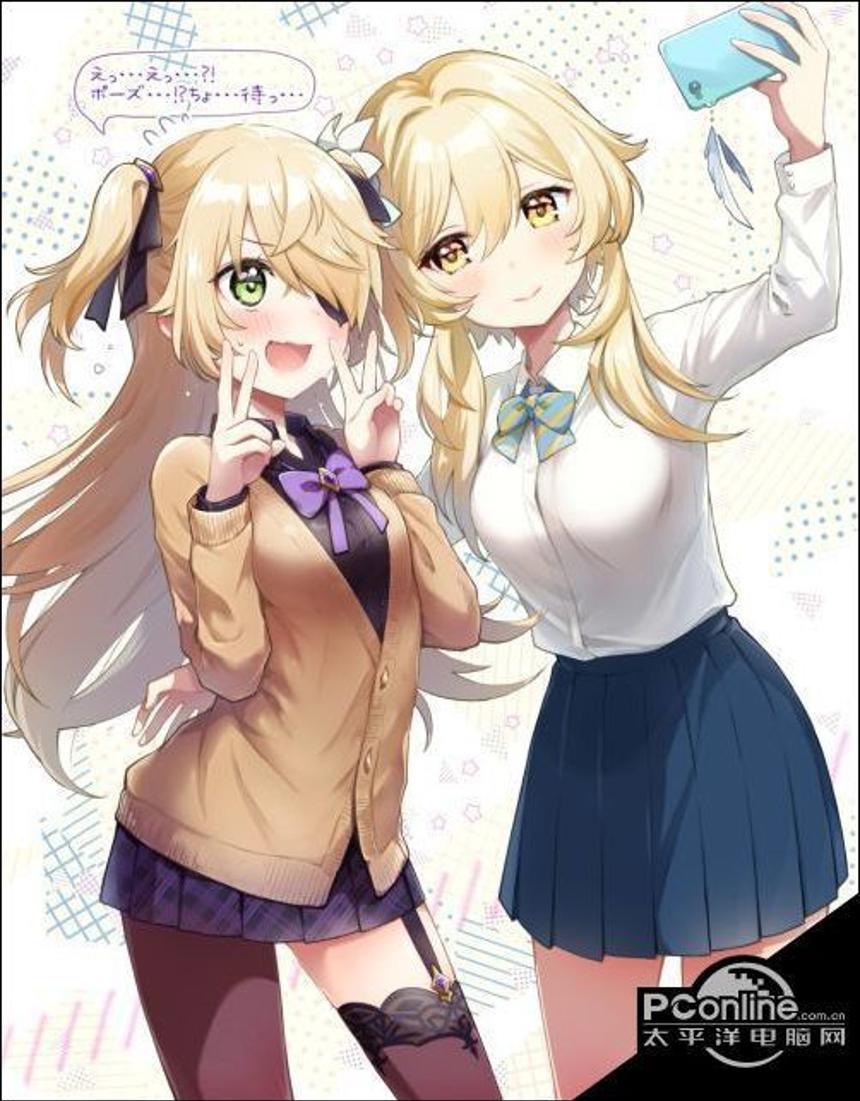
 明日方舟工口博士日常
明日方舟工口博士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