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水仙碱.(2)
“戒香!”他平生第一次喊出了那个只有梦里才敢不加称谓呢喃着念出的名字。戒香面带笑意,羞涩地低下了头。如果现在哭出来的话,不论是谁都会觉得他的眼泪竟如此轻贱,而因此对他心生鄙夷吧,可他谁也不顾了,倘若硬要说他的眼泪有什么顾忌,那就只有不要让泪模糊了眼中的戒香罢了。
他走上前,戒香将手搭在他的胸口,似乎温和地告诫着他不许再靠近了,他的袖口上、领口上统统扎上了鬼针草。身着西装的男士不知何时已转过身背对着二人,原来他西装背面是纯正的黑色。
戒香指指天花板。他诧异地望着单调的天花板上挖出来的一块一米见方的星空,本应被铁板封住的天窗此刻向他们敞开,从此处登上去便是没有围栏的天台。即使奋力跳起,他也触摸不到天花板的边缘,更不要说让他扒住天窗爬上去了。他朝戒香摆摆手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走廊最不起眼的深处走出来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他知道她对自己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女人,但他却认定了,此般难题非这完全陌生的女人不可解决。
她跪在自天窗射入的正方形的月光里,伸出交叠在一起的双手。戒香压低声音说失礼了,就以那手掌为阶梯踩了上去,完全陌生的女人双腿剧烈地颤动,摇晃着才勉强伸直腿,不过已经足够了,戒香轻而易举迈步走上天台。
等到他也在完全陌生的女人帮助下登上天台的时候,他和戒香两人跪在天窗两侧向着白西装和女人告别。他忽然想起自己还没有和女人交换名字,就让她消失在漆黑的走廊当中去了。
“起风了。”
他的胃痛到了几乎难以忍受的境地,控制着抽搐不止的双手,他勉强脱去了外套,拿手掌固执地掸掉仍挂在上面的鬼针草,示意戒香钻进来。外套仅仅足够揽住他们二人的肩膀,也让他们得以依偎在一起。
他走上前,戒香将手搭在他的胸口,似乎温和地告诫着他不许再靠近了,他的袖口上、领口上统统扎上了鬼针草。身着西装的男士不知何时已转过身背对着二人,原来他西装背面是纯正的黑色。
戒香指指天花板。他诧异地望着单调的天花板上挖出来的一块一米见方的星空,本应被铁板封住的天窗此刻向他们敞开,从此处登上去便是没有围栏的天台。即使奋力跳起,他也触摸不到天花板的边缘,更不要说让他扒住天窗爬上去了。他朝戒香摆摆手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走廊最不起眼的深处走出来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他知道她对自己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女人,但他却认定了,此般难题非这完全陌生的女人不可解决。

她跪在自天窗射入的正方形的月光里,伸出交叠在一起的双手。戒香压低声音说失礼了,就以那手掌为阶梯踩了上去,完全陌生的女人双腿剧烈地颤动,摇晃着才勉强伸直腿,不过已经足够了,戒香轻而易举迈步走上天台。
等到他也在完全陌生的女人帮助下登上天台的时候,他和戒香两人跪在天窗两侧向着白西装和女人告别。他忽然想起自己还没有和女人交换名字,就让她消失在漆黑的走廊当中去了。
“起风了。”
他的胃痛到了几乎难以忍受的境地,控制着抽搐不止的双手,他勉强脱去了外套,拿手掌固执地掸掉仍挂在上面的鬼针草,示意戒香钻进来。外套仅仅足够揽住他们二人的肩膀,也让他们得以依偎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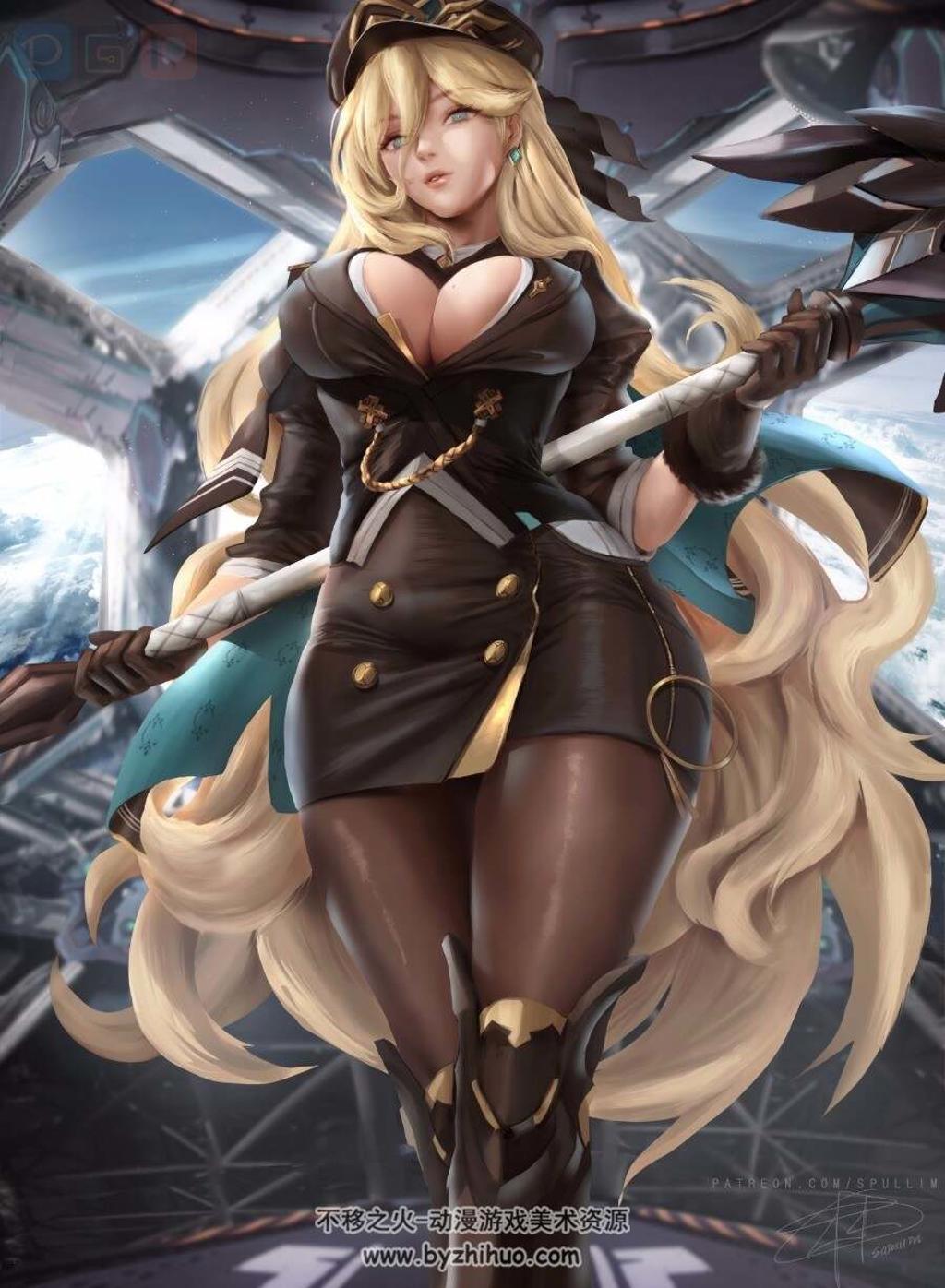
 冰秋捆仙绳车
冰秋捆仙绳车


















![[华晨宇水仙文]《温桃歌》第一章秋夜](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202/145213_75051.jpg)
![[华晨宇水仙文]《温桃歌》第一章秋夜](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506/164101_86122.jpg)
![[华晨宇水仙文]《温桃歌》第一章秋夜](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522/162417_04440.jpg)
![[华晨宇水仙文]《温桃歌》第一章秋夜](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619/112036_11041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