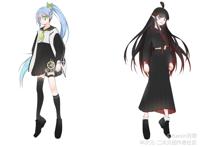The Beginning(4)
这让春感到很受伤。那是一间温室,一座人类建给花儿们住的玻璃小房子,而温室中的花草是不需要他的。不然他又何以被拒之门外呢。
春沿着小房子一侧继续前行,对于所处方位仍然一头雾水。或许这里才更像是另一个世界,竟连他都因不曾光顾而在此迷路了。
绕过转角处一株直愣愣的小胡桃树和一大丛古怪的杂色月季后,他发觉自己来到了温室正面。一条卵石小径蜿蜒穿过草地,由紧锁的温室门通向围墙外,路的一侧还种着向日葵。花儿已经结籽,不复昔日挺拔的身姿和金灿灿流光溢彩的面庞;虽然太阳还分明悬垂在地平线之上,这些高大的,在人们眼中矢志不渝追随光和热的花却齐齐背朝西方。它们低垂头颈,悉心呵护着幼弱的种子;倘使一个不慎,希望便会随着哪日正午的骄阳,在自己手中化为乌有。
这些种子,劳它们耗尽心血,有多少种壳内只是空空如也,又有多少能够重归泥土,最终如花儿所愿,延续它们短暂卑怜的生命。仅仅一厢情愿罢了,不知情的人会怎么说呢?但花儿不在乎这些,因为对于它们,那承载了一切,是比生命还要宝贵,比光明更值得珍视千百万倍的东西。
按照向日葵花盘的指向,他重又找回来时的路。
西北方的天边像是挂着一口快燃尽的炉子,晚霞由赤铜色冷却为深绛,头顶和稍远处的灰云在风中变换着形状,宛如一只只鼓动翅膀扑向余烬的大飞蛾。春栖身在凡恩街6号屋顶,背倚着烟囱,等待暮色笼罩尼伯维尔。之前那趟短暂的游历唤起许多早已遗忘的东西,这体验他好久没有过了,只可惜他不久后就要离开,到更北的地方去。喧腾的世界他永远看不到,只能由夏讲给他听,而她又一向那么不善于表达。“唉——”春不由发出一声轻叹,尽管心中并不很感到忧愁。所有杨柳的枝条都在洋槐花气味的风中幸福地荡漾着。
突然院子里一阵喧闹,引得春向屋檐凑过去。喧声无疑来自许多孩子,他们晚饭后的玩耍时间到了;可是等等,这里住的不是那个父母们避而远之的疯子吗?他家何时变得这样热闹了?
春探身向下瞧,只见一只绿色的小家伙蹦蹦跳跳跑到草坪中央,动作和形貌都是前所未见的奇特,以致有那么一瞬引发了他一种可笑的联想——一株长脚的豌豆;但他接着就看到它在用什么转身:不是四肢也不是腕足,而是四片又大、又壮的叶子。
他们几乎猝然间就四目相对了,春的震惊可想而知,正当他试图回避并且疑惑刚才的喧嚷是否发自对方时,小家伙清亮地一声喊出了这家主人的名字:
春沿着小房子一侧继续前行,对于所处方位仍然一头雾水。或许这里才更像是另一个世界,竟连他都因不曾光顾而在此迷路了。
绕过转角处一株直愣愣的小胡桃树和一大丛古怪的杂色月季后,他发觉自己来到了温室正面。一条卵石小径蜿蜒穿过草地,由紧锁的温室门通向围墙外,路的一侧还种着向日葵。花儿已经结籽,不复昔日挺拔的身姿和金灿灿流光溢彩的面庞;虽然太阳还分明悬垂在地平线之上,这些高大的,在人们眼中矢志不渝追随光和热的花却齐齐背朝西方。它们低垂头颈,悉心呵护着幼弱的种子;倘使一个不慎,希望便会随着哪日正午的骄阳,在自己手中化为乌有。
这些种子,劳它们耗尽心血,有多少种壳内只是空空如也,又有多少能够重归泥土,最终如花儿所愿,延续它们短暂卑怜的生命。仅仅一厢情愿罢了,不知情的人会怎么说呢?但花儿不在乎这些,因为对于它们,那承载了一切,是比生命还要宝贵,比光明更值得珍视千百万倍的东西。
按照向日葵花盘的指向,他重又找回来时的路。

西北方的天边像是挂着一口快燃尽的炉子,晚霞由赤铜色冷却为深绛,头顶和稍远处的灰云在风中变换着形状,宛如一只只鼓动翅膀扑向余烬的大飞蛾。春栖身在凡恩街6号屋顶,背倚着烟囱,等待暮色笼罩尼伯维尔。之前那趟短暂的游历唤起许多早已遗忘的东西,这体验他好久没有过了,只可惜他不久后就要离开,到更北的地方去。喧腾的世界他永远看不到,只能由夏讲给他听,而她又一向那么不善于表达。“唉——”春不由发出一声轻叹,尽管心中并不很感到忧愁。所有杨柳的枝条都在洋槐花气味的风中幸福地荡漾着。
突然院子里一阵喧闹,引得春向屋檐凑过去。喧声无疑来自许多孩子,他们晚饭后的玩耍时间到了;可是等等,这里住的不是那个父母们避而远之的疯子吗?他家何时变得这样热闹了?
春探身向下瞧,只见一只绿色的小家伙蹦蹦跳跳跑到草坪中央,动作和形貌都是前所未见的奇特,以致有那么一瞬引发了他一种可笑的联想——一株长脚的豌豆;但他接着就看到它在用什么转身:不是四肢也不是腕足,而是四片又大、又壮的叶子。
他们几乎猝然间就四目相对了,春的震惊可想而知,正当他试图回避并且疑惑刚才的喧嚷是否发自对方时,小家伙清亮地一声喊出了这家主人的名字:

 ao3fog
ao3f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