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邪】年关来客(一)(2)
奇怪的是,他没有立刻回答我,也没有像平时一样欠揍地冷笑连连,我听见他在剧烈地咳嗽。
过了好半天,他缓过来,才能说出话,“当然是讨债来了,吴邪,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清楚吗?”
不等我回答,他又道,“你最好马上到这里来,不然后面发生什么事情,我可无法保证。”说完,就听他对身边人说,“陈警官,您放心,吴老板说他立刻赶过来。”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放下手机,开始深呼吸,吐了半天气还是觉得胸口发胀。这个死孩子总有办法气得我五脏六腑都疼,等我过去,绝对让闷油瓶摁住他,然后开个直播间,让他所有手下看着我直播打他们老板的屁股。
闷油瓶一直在我旁边静静听着,看我这样,并没有多问,只是很贴心地伸手帮我按摩后颈,帮我平静下来。
在闷油瓶身边待得久了,我渐渐发现张家在很多奇奇怪怪的方面都有常人无法想象的造诣,比如像这样通过按压穴位迅速让人平静。
还有一次,家里的鸡长大了,每天四五点就疯狂打鸣,我向闷油瓶反映过一次之后,他可能是怕我一怒之下杀了他的爱宠,就进山采了几株叶子非常肥厚的怪草,碾碎了拌在鸡饲料里,硬是把人家的打鸣时间延到了七点以后。这直接导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他格外体贴温顺,生怕他一时不爽就搞些什么偏方用在我身上。
伴随着颈后的按摩,我的大脑渐渐归位,于是,我打出了第一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我一位在体制内工作的高中同学,他的职位我在此不能详说,但如果真的有条子来我铺子里执行公务,他一定会得到消息。就算黎簇带来的是外地条子,这样跨市跨省的公务,报批过程中也一定会经我同学的手。
好消息是,我同学对此一无所知。甚至他让我保持通话等了十分钟,待他细细查了一番回来,依旧没有查到任何官方信息。
按照他的猜测,如果黎簇和纽扣都没有撒谎,那么那位陈警官多半不是为公务来的。
话到此处,我放下了半颗心,打出了第二个电话。
电话嘟了一声,对方就迅速接起。
“老板!”王盟在对面笑嘻嘻,“你是终于想通要回杭州过年了吗?”我顿时无语,恨不得沿着信号基站一路辐射过去把他的脸打出花儿来。
原来这厮嫌纽扣太啰嗦,把人家全方位拉黑了,纽扣找不到他,坎肩白蛇几个不是在外地,就是也打不通电话(我深深怀疑不止王盟一个人拉黑了他),他又急又怕,这才找到我这里。
我叹一口气,难怪二叔总说我这些伙计没有一个是靠谱的。我当初因为年轻时走了太多聪明人画的弯路,选人时十分倔强地只考量了忠心这一条,这几年时不时就孽力回馈一次。
过了好半天,他缓过来,才能说出话,“当然是讨债来了,吴邪,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清楚吗?”
不等我回答,他又道,“你最好马上到这里来,不然后面发生什么事情,我可无法保证。”说完,就听他对身边人说,“陈警官,您放心,吴老板说他立刻赶过来。”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放下手机,开始深呼吸,吐了半天气还是觉得胸口发胀。这个死孩子总有办法气得我五脏六腑都疼,等我过去,绝对让闷油瓶摁住他,然后开个直播间,让他所有手下看着我直播打他们老板的屁股。
闷油瓶一直在我旁边静静听着,看我这样,并没有多问,只是很贴心地伸手帮我按摩后颈,帮我平静下来。
在闷油瓶身边待得久了,我渐渐发现张家在很多奇奇怪怪的方面都有常人无法想象的造诣,比如像这样通过按压穴位迅速让人平静。
还有一次,家里的鸡长大了,每天四五点就疯狂打鸣,我向闷油瓶反映过一次之后,他可能是怕我一怒之下杀了他的爱宠,就进山采了几株叶子非常肥厚的怪草,碾碎了拌在鸡饲料里,硬是把人家的打鸣时间延到了七点以后。这直接导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他格外体贴温顺,生怕他一时不爽就搞些什么偏方用在我身上。

伴随着颈后的按摩,我的大脑渐渐归位,于是,我打出了第一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我一位在体制内工作的高中同学,他的职位我在此不能详说,但如果真的有条子来我铺子里执行公务,他一定会得到消息。就算黎簇带来的是外地条子,这样跨市跨省的公务,报批过程中也一定会经我同学的手。
好消息是,我同学对此一无所知。甚至他让我保持通话等了十分钟,待他细细查了一番回来,依旧没有查到任何官方信息。
按照他的猜测,如果黎簇和纽扣都没有撒谎,那么那位陈警官多半不是为公务来的。
话到此处,我放下了半颗心,打出了第二个电话。
电话嘟了一声,对方就迅速接起。
“老板!”王盟在对面笑嘻嘻,“你是终于想通要回杭州过年了吗?”我顿时无语,恨不得沿着信号基站一路辐射过去把他的脸打出花儿来。
原来这厮嫌纽扣太啰嗦,把人家全方位拉黑了,纽扣找不到他,坎肩白蛇几个不是在外地,就是也打不通电话(我深深怀疑不止王盟一个人拉黑了他),他又急又怕,这才找到我这里。
我叹一口气,难怪二叔总说我这些伙计没有一个是靠谱的。我当初因为年轻时走了太多聪明人画的弯路,选人时十分倔强地只考量了忠心这一条,这几年时不时就孽力回馈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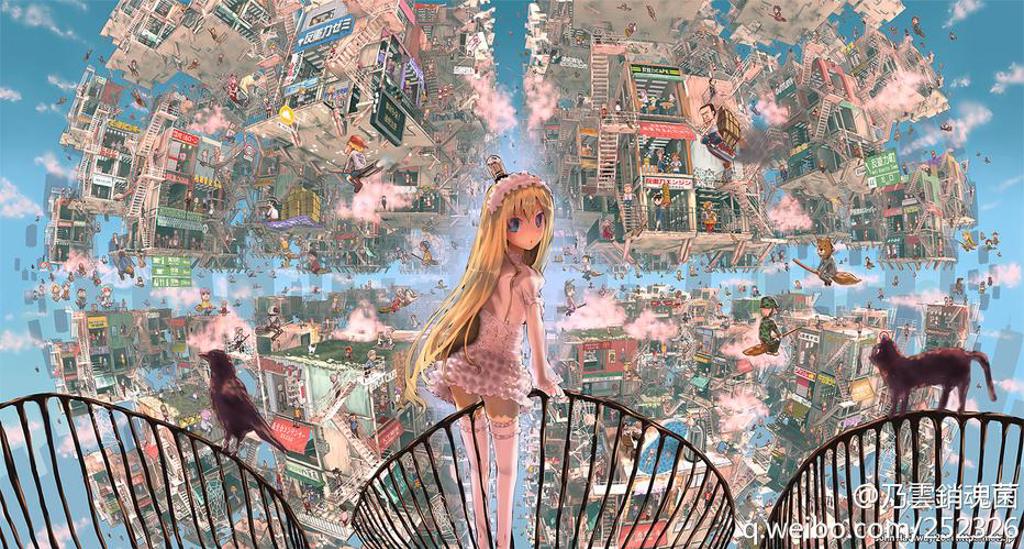
 邪瓶r车writeas
邪瓶r车write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