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Umy」佛罗伦萨没有爱情(2)
不知为什么我竟有些手足无措,然后落荒而逃。
我在佛罗伦萨租了个二楼的小公寓,但我不能安于客枕,前几日的生活让人忙得昏天黑地。那时我还没有习惯橄榄油的味道,所以依仗速食食品过活。但我的确从没想过会在上学路上的便利店里再遇到她。
我才知道原来她在这里打工。揭去黄昏的皮囊,在惨淡的白炽灯下,影子很像濒死的飞蛾,我得以真正窥见她的样子。
她的眼睛很漂亮,是所有奔死之人都愿意纵身跃下的那类河流。
不知是否该称为幸运,她似乎并没有忘了我,反而向我问候近来可好,我支吾着回答,出于对美的感知,有一些别的问题呼之欲出:你是谁?你一个人吗?你要不要和我一起?
直到那天为止,我仍然站在很冷的秋天里,没有跌进那条使我再起不能的长河。
我不过多赘叙,在此直接复述结果:她给予了我肯定的答案。
大约两天以后,她带着为数不多的行李搬进了我的公寓,在这四十八小时里我有意无意地开始给她留出一个足够舒适的位子,除了我的画室之外,许多物件都被迫拥挤在了一起,她再次对我的邀约表达感谢,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开始拟定生活的正轨。
她得知我此行目的后少许调侃地笑了:喔——是大画家。
最初我还会尴尬地辩解,后来便由着她七零八落地编篡奇怪的称呼。
她是个很自由的人。这是我后来认定的,自由地流浪、自由得像没有明天一样地唱,街头演唱和便利店的兼职成了她经济的来源,她偶尔会起得比我都早,然后背着那把生冷的吉他出门,浸着烟草味的影子要到午夜才回到灯下。我不是这样的,我永远在精疲力竭地学习、精疲力竭地作画、精疲力竭地生活,而不是她那样精疲力竭仍在歌唱。
家人对我功成名就的要求引着我的每支笔都滑向阴暗的后巷,墙根也开不出任何一朵花。
终于有某个尘埃都漂浮不起来的下午,我本还在画板前燃烧焦虑感,在被这种郁苦烫伤的空隙,我侧着身子看到她窝在沙发一角无意义地重复游戏的死局。
那里你已经错了七次了吧。
嗯?是吗? 她望向我的眼神仍像一只鸽子,灵动且可以高飞。 那你画出一张画了吗?
...没有。 我盯着眼前一片虚无,感觉世界又要再次开始生锈。
你离世俗太远啦,我的大艺术家。 她笑了笑,话到此被截停了。
那天之后,我偶尔会跟着她一起去街头写生,再将画子以一些并不漂亮的价格卖出去。您可能难以理解,这在当时的我是鲜少想象的,他们总喜欢将艺术摘得太高,以至于在很久以前我和她做过一些关于为什么她要做街头歌手的讨论,我甚至条件反射地惊讶于她所说的“喜欢和赚钱是什么冲突的事情吗?”我才意识到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习惯于将艺术爱好架上理想高台,而仿佛理想就该高于世俗,不然就会暴亡生出白骨。我先前读过一些书,也太习惯从文学寻找灵感与慰藉,可居然从未绕过书本看看人间。
我在佛罗伦萨租了个二楼的小公寓,但我不能安于客枕,前几日的生活让人忙得昏天黑地。那时我还没有习惯橄榄油的味道,所以依仗速食食品过活。但我的确从没想过会在上学路上的便利店里再遇到她。
我才知道原来她在这里打工。揭去黄昏的皮囊,在惨淡的白炽灯下,影子很像濒死的飞蛾,我得以真正窥见她的样子。
她的眼睛很漂亮,是所有奔死之人都愿意纵身跃下的那类河流。
不知是否该称为幸运,她似乎并没有忘了我,反而向我问候近来可好,我支吾着回答,出于对美的感知,有一些别的问题呼之欲出:你是谁?你一个人吗?你要不要和我一起?
直到那天为止,我仍然站在很冷的秋天里,没有跌进那条使我再起不能的长河。
我不过多赘叙,在此直接复述结果:她给予了我肯定的答案。
大约两天以后,她带着为数不多的行李搬进了我的公寓,在这四十八小时里我有意无意地开始给她留出一个足够舒适的位子,除了我的画室之外,许多物件都被迫拥挤在了一起,她再次对我的邀约表达感谢,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开始拟定生活的正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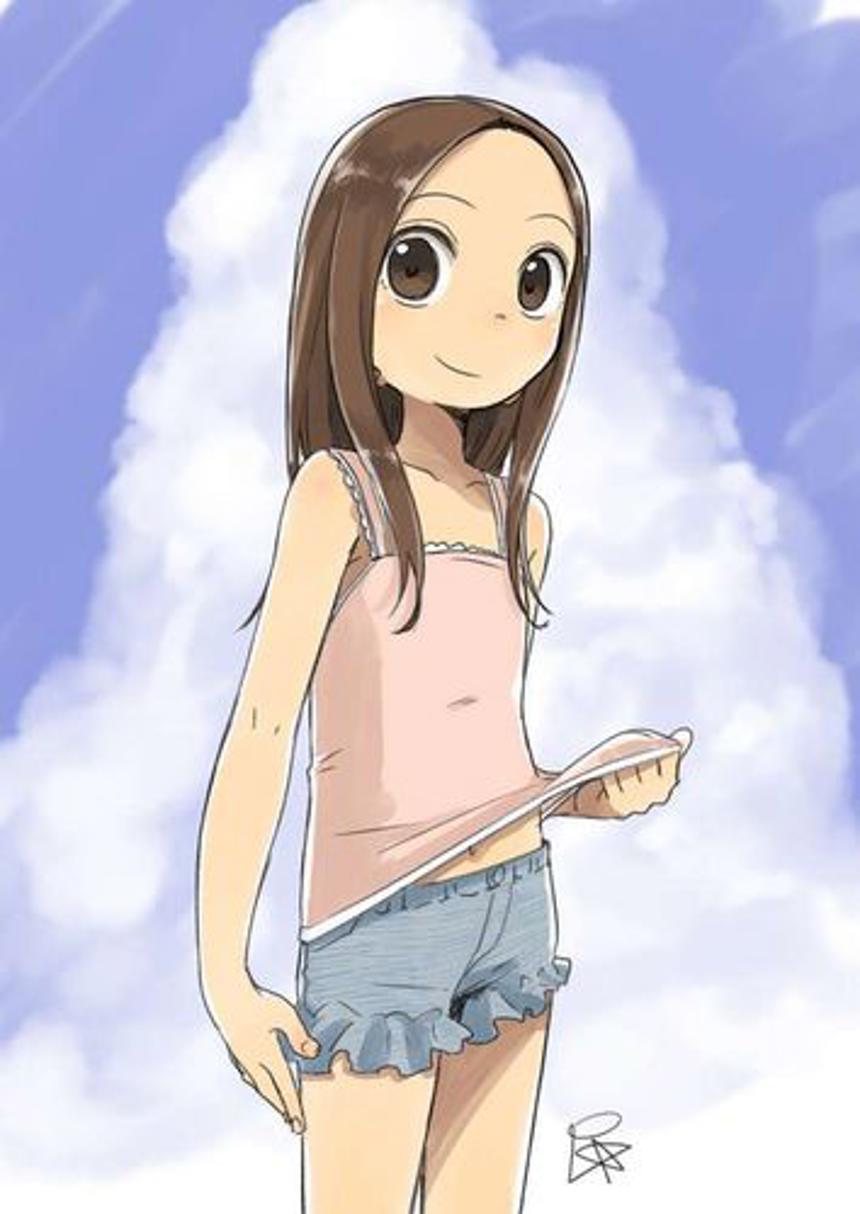
她得知我此行目的后少许调侃地笑了:喔——是大画家。
最初我还会尴尬地辩解,后来便由着她七零八落地编篡奇怪的称呼。
她是个很自由的人。这是我后来认定的,自由地流浪、自由得像没有明天一样地唱,街头演唱和便利店的兼职成了她经济的来源,她偶尔会起得比我都早,然后背着那把生冷的吉他出门,浸着烟草味的影子要到午夜才回到灯下。我不是这样的,我永远在精疲力竭地学习、精疲力竭地作画、精疲力竭地生活,而不是她那样精疲力竭仍在歌唱。
家人对我功成名就的要求引着我的每支笔都滑向阴暗的后巷,墙根也开不出任何一朵花。
终于有某个尘埃都漂浮不起来的下午,我本还在画板前燃烧焦虑感,在被这种郁苦烫伤的空隙,我侧着身子看到她窝在沙发一角无意义地重复游戏的死局。
那里你已经错了七次了吧。
嗯?是吗? 她望向我的眼神仍像一只鸽子,灵动且可以高飞。 那你画出一张画了吗?
...没有。 我盯着眼前一片虚无,感觉世界又要再次开始生锈。
你离世俗太远啦,我的大艺术家。 她笑了笑,话到此被截停了。
那天之后,我偶尔会跟着她一起去街头写生,再将画子以一些并不漂亮的价格卖出去。您可能难以理解,这在当时的我是鲜少想象的,他们总喜欢将艺术摘得太高,以至于在很久以前我和她做过一些关于为什么她要做街头歌手的讨论,我甚至条件反射地惊讶于她所说的“喜欢和赚钱是什么冲突的事情吗?”我才意识到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习惯于将艺术爱好架上理想高台,而仿佛理想就该高于世俗,不然就会暴亡生出白骨。我先前读过一些书,也太习惯从文学寻找灵感与慰藉,可居然从未绕过书本看看人间。
 有没有斗罗小说是双男主的小说
有没有斗罗小说是双男主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