囿于窗棂的月光

儿时的月亮,飞啊飞啊,飞到我日思夜想的梦乡。
——题记
对于一个儿时因火炮失去双腿的人来说,在阳光下奔跑是一件奢侈的事。
万幸的是截肢的时候我才三岁多一点,那时还没有痛苦的记忆,只知道记事以来,时常坐在轮椅上,掐着自己空荡荡的裤管发呆。
或许因为天生有别,我在白天呼呼大睡,到了晚上反而格外精神。在大人们睡着了以后,我蹭的从木床上撑起自己,有一瞬间觉得自己的腿还在,我必是要等着她的。鸣蜩和蛙鸣里,童年的月亮就从树梢一点一点爬上来,有时大如盘,有时又细如钩,月亮滴下一滴华彩在平房小屋的窗纸上,月光渐渐把不透明的纸润的通亮。我这时能看见她了,透过一层薄薄的面纱,那温婉如玉的美更勾的人几分沉醉。
这时推开窗,那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便顿时不在,最先扑入怀中的,是清凉的甘月,和清朗的香风。月下,安睡的村庄也变得清晰,从这能直接看到路口睡熟的大黄,大黄身后不远微漾的稻浪。掰出手指头数,这边的瓜田曾跟二狗一起偷过瓜——虽然我是放哨的那个,那边的池塘曾被小胖丢过一只鸡——说是要给它洗个澡……我伏在窗边,伸出小手,月亮像蝴蝶一般栖止在掌心,我于是就抓住了月亮,我把她小心地别在窗边,欣赏着自己伟大的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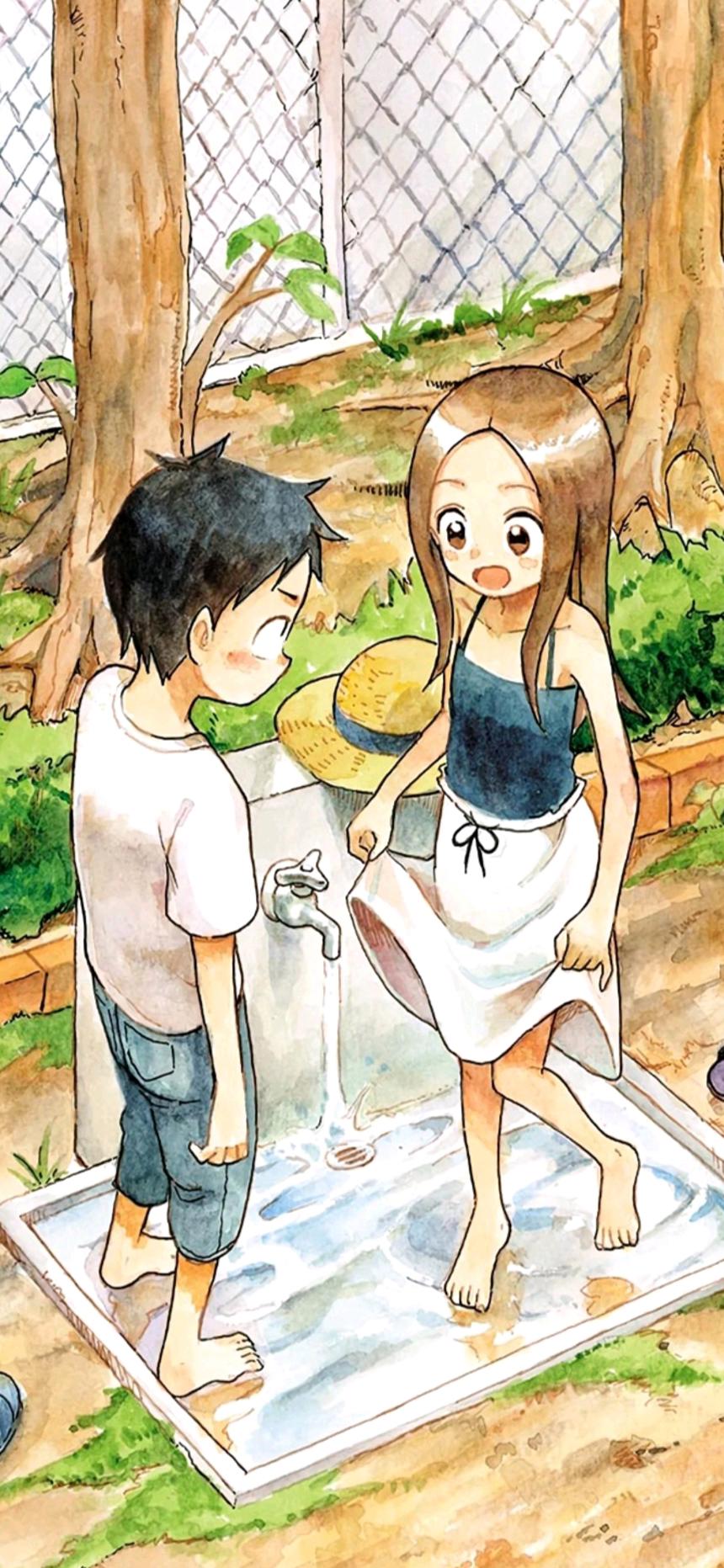
 托着足月的孕肚做扩产
托着足月的孕肚做扩产


